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文章已被收录到落日间,落日译介。详情请见:点击跳转
译者按:
译者按:
游戏与殖民,这两个看似不是很对付的概念在今天游戏逐渐传播到世界的各个文化时偶然的碰到了一起。本文作者Souvik Mukherjee作为一个印度学者深刻的讨论了游戏设计时出现的跨文化难题。刺客信条作为一款由欧洲公司育碧开发的游戏,在旗下游戏DLC《黑旗—自由呐喊》中大胆的设计了由黑人奴隶为主角的故事。此时在游戏中,欧美的游戏设计师作为当年的殖民者和玩家作为游戏中的奴隶形成了鲜明的殖民对比。如果把游戏看成是魔圈,那么好像此时的玩家和制作者没有特别的关联。但当游戏的故事切身的影响到了玩家本身的文化和政治,比如最近讨论激烈的《刺客信条:影》中的黑人与日本武士,似乎火药味就变得相当浓重。Mukherjee就制作者作为游戏世界中的殖民者和玩家作为游戏世界中可能的反抗者重塑了玩家和制作者游戏内外的政治关系和身份。所以当游戏真正开始映射历史,那游戏与殖民将不再遥远,它们可能就是重新假设昨天的你我。
本文主要讨论的概念是后殖民主义。即是讨论殖民,那就会有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关系。Mukherjee主要以欧美和印度这对现实中的殖民关系讨论欧美游戏中是如何重现这段关系的。当然游戏的设计是相对的。既然有欧美设计印度的游戏,那自然印度也有反过来描述欧美殖民者的游戏。这两种视角不仅会改变制作者和玩家的关系定位,也会让玩家更加真切的感受到不同视角下游戏叙事的不同。当然,Mukherjee也用了很多其它的学术讨论充实这个后殖民主义的核心讨论,比如加入Said的东方主义、Gajjala所讨论的属下阶层、还有Nakamura讨论的网络中的身份旅行(Identity Tourism)。希望各位看得开心。
作者简介:Souvik Mukherjee 是印度加尔各答社会科学研究中心的文化研究副教授。Souvik 通过电子游戏作为叙事媒体所传递的话语研究探讨叙事和文学,并研究这些游戏如何影响和挑战我们对叙事、身份和文化的理解。他的相关兴趣和专长涵盖游戏研究中的诸多主题:包括从电子游戏和棋盘游戏中所表现的后殖民主义、身份和时间性以及东南亚的电子游戏产业。Souvik 是三本专著的作者:《Videogames and Storytelling: Reading Games and Playing Books》(Palgrave Macmillan 2015)、《Videogames and Postcolonialism: Empire Plays Back》(Springer UK 2017)和《Videogames in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Development, Culture(s) and Representations》(Bloomsbury India 2022),目前他正在进行一本关于印度棋盘游戏和殖民主义的书籍项目。
以下是正文与翻译:
- 摘要
后殖民主义仍然处于游戏研究的边缘,尽管当代关于种族、性别和其他挑战传统规范的辩论已经被广泛纳入其中。然而,很难相信它没有定义视频游戏的认知方式;可以说,其影响是微妙的。对于数百万玩《帝国:全面战争》或《东印度公司》这类游戏的印度人来说,考虑到他们从学术界到日常对话中无处不在的后殖民反应,这些玩家对游戏中殖民历史的体验是直接且不可避免的。电子游戏构建空间性、政治系统、伦理和社会观念的方式往往深受殖民概念的影响,因此也包含对现实中殖民主义的质疑。本文旨在探讨电子游戏中包含潜在的后殖民主义所带来的复杂性,以及我们如何解读这些游戏。
- 后殖民思维与电子游戏:导论
尽管当代关于种族、性别和其他挑战传统规范的辩论已经被广泛纳入了游戏研究,后殖民主义仍然处于游戏研究讨论的边缘。然而,很难相信后殖民主义的思想不会影响人们对电子游戏的认知;可以说,其影响往往是微妙的。对于数百万印度玩家来说,他们在玩《马克思·佩恩3》(2012)或《刺客信条》(2007)时是否会受到殖民历史的影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然而,当他们玩《帝国:全面战争》(2009)或《东印度公司》(2009)等游戏时,他们对殖民历史的体验是直接且不可避免的。同样地,叙利亚青年在玩《美国陆军》(2002)或玩诸如《灰烬之下》这样的mod,以及中非的玩家在玩《孤岛惊魂2》(2008)时,可以预见他们会接触到与权力和殖民化话语相关的独特政治意识。本文旨在探讨某些电子游戏构建空间性、政治系统、伦理和社会观念的复杂方式,这些方式往往深受殖民概念的影响,因此也包含对殖民主义的质疑。
本文将以Lisa Nakamura(2002)关于电子游戏中种族的研究,Sybille Lammes(2010)和Shoshana Magnet(2006)关于电子游戏中后殖民空间性的研究,以及我自己早期关于电子游戏中殖民制图的论文(Mukherjee,2015)为出发点,同时也会涉及Homi Bhabha(1994)、Edward Said(1979)和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1999)等评论家的当前后殖民理论。“后殖民主义”一词本身需要在这里作些解释。Ashcroft和Tiffin认为它是“帝国文化与本土文化实践之间的互动”,并且是一个“涵盖殖民过程所有方面的术语,从殖民接触的开始一直到现在”(Ashcroft,Griffiths,& Tiffin,2005,第2页)。在讨论这一概念与电子游戏的关系之前,还需要简要谈论一下本文标题中的一个关键词:“属下阶层/底层”(subaltern)。这个概念是由Ranajit Guha领导的一组历史学家和理论家从Antonio Gramsci那里借来的,他们致力于撰写“自下而上的历史”,并“自觉努力纠正社会历史中传统的精英阶层视角的偏见”(Arnold,Bayly,Brass,& Chakravarty,2012,第13页)。Spivak在其开创性的文章《底层能说话吗?》中指出,将属下阶层人民视为抗议的“核心”或本体论上明确界定的实体存在风险。相反,Spivak认为属下阶层人是一个无法自我表达的声音。评论家们指出,“没有一个属下阶层主体能够认识并表达自己”(Nelson & Grossberg 1988,第27页)。
考虑到上述关于后殖民主义和属下阶层人民的立场,本文的论点将是对电子游戏中后殖民主义的三重考察,并探讨电子游戏如何成为一种属下阶层性质的媒介。第一部分将探讨即时战略游戏中的地图表现,以及它们如何延续殖民定义地缘政治的方式。重要的是,电子游戏中出现的替代历史和地图可能作为一种潜在话语挑战上级殖民框架。论点的第二个部分将从后殖民的角度探讨电子游戏中的身份构建。最后,本文将审视电子游戏中“东方”的认知和表现,以及了解促使游戏开发者在其游戏中包含此类表现同时抹去某些元素的原因。
过去的文献分析分别探讨了后殖民游戏中的地图元素或身份构建,本文的目的是研究后殖民思维如何通过链接外部理解和自我反思性认知达到统一后殖民主体认知。通过理解后殖民主体的观点,殖民霸权的反应以及这些反应的问题,本文将说明抗议的过程以及属下阶层性。最后,本文分析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后殖民主体是如何通过电子游戏及其玩家的视角重新定义的。
- 电子游戏地图制图与后殖民
殖民帝国常常被形容为一种游玩。19世纪在中亚探险和标记潜在领土的探险家们,将他们为英俄领主进行的间谍活动、监视和制图称为“伟大的游戏”或“阴影之战”(Hopkirk,2006)。这个短语由鲁德亚德·吉卜林在其小说《基姆》中推广,据称源于一位名为Stoddart的上校,他在想到这个比喻时,可能联想到的是英式橄榄球。与(或许是杜撰的)关于滑铁卢战役“伊顿公学的操场”评论相似,这个术语似乎暗示了一种按相互同意的规则进行的超乎人命的活动。显而易见的游戏性巧妙的隐藏了许多严肃且能改变世界的内容。在吉卜林的小说中,Kim通过神秘的Lurgan Sahib大师学习,习得了一种宝石游戏——这个游戏在不知不觉中教会了他在未知领土探索的技能。同样的游戏体验,如《帝国时代》或《海岛大亨》(PopTop Software,2001)等游戏,含沙射影地将玩家带入了关于殖民主义和占领土地的巨大权利架构中。
评论者普遍认为,电子游戏与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有关,他们声称这些游戏本质上与殖民主义和帝国有联系。根据Andrew Baerg(2009年)的观点,“数字游戏及其计算表示过程,执行驱动符号系统的规则,代表了新自由主义中的过程”(第119页)。他引用Ian Bogost(2010)的程序修辞概念,即“计算机处理、计算和操作大量基于规则的符号的能力”(Baerg,2009,第119页),以使我们能够理解“我们周围世界的运作,并且这个运作过程能够影响和潜在地说服我们”。Baerg认为,电子游戏的程序修辞产生了一种双向的影响:首先,它反映了自由市场逐步扩展和选择的过程;其次,这些选择背后有经济上的理性。这一分析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适用于所有电子游戏;相反,这个理论关注的是那些与上述影响框架相关的许多游戏,无论是明显相关的游戏或是那些未被挑明此关系的游戏。以具体的对比为例,Magnet对《海岛大亨》的评论清楚地指出了游戏机制背后的类似原则(政治经济影响):
《海岛大亨》的资源被称为你的资源——包括其公民。尽管游戏明确指出你的人民拥有自由意志,但它提醒你,他们可以通过你的金钱诱导听从你的命令——或者在这种策略失败时,通过军事力量。你甚至可以实行戒严。资本主义是游戏的核心内容。(Magnet,2006,第144页)
这些游戏特点本身反映了与殖民地相似的帝国机制,尽管带有一点讽刺和批判意味。《海岛大亨》是一个岛屿,尽管帝国主义势力已经离去,帝国的过程依然以不同方式继续。政治理论家Michael Hardt和Antonio Negri(2001)谈到类似现象时宣称:“伴随着全球市场和全球生产回路的出现,出现了全球秩序,一种新的逻辑和统治结构——简而言之,一种新的主权形式”(第xi页)。他们称这种调节全球交换的权力为帝国。
在原则上,电子游戏仍然存在与殖民帝国的相似性。尽管世界地图上表示各个帝国的红色、蓝色和绿色区域已经消失,研究电子游戏如何以各种形式——现代和殖民——表现帝国原则都还是有益的。这样思考游戏能够更好地阐明和发展当前对于游戏研究的评论。谈到地图,制图一直是殖民空间建构的关键元素。而帝国建设类电子游戏中的地图建构,如《帝国时代》系列(1997-2014)、《帝国:全面战争》(2007)、《国家的崛起》(2003)和《地球帝国》(2001)等,提供了一个引人入胜的视角。谈到地图在殖民扩展中的作用,Tom Bassett指出:
非洲的制图划分与制图和帝国建设密不可分。然而,在地图上画线的行为只是制图推动帝国主义的一个例子。地图曾被用来以各种方式扩展欧洲对外国和未知领土的霸权。(Bassett,1994,第316-335页)
事实上,由乔治·埃弗里斯特上校领导的印度大三角测量是英国殖民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学家John Keay(2000)称其为“树干、骨架的脊柱[…],在其精确绘制位置的基础上,所有其他调查和位置都依赖它”(第xix页)。埃弗里斯他(Everest)将他的名字赋予了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如同“命名”珠穆朗玛峰一样,命名行为对帝国扩张议程具有重要意义。同样的,这种明明行为也适用于树立旗帜和设立景观。正如英国单口喜剧演员Eddie Izzard在其作品《你有旗子吗?》中精彩地笑道:“我们对旗子的巧妙使用控制了其它国家!是的,只需航行到世界各地插上旗子,然后我宣称印度为英国所有!”(Jordan,1999)。在《植物帝国》(2011)中,Eugenia Herbert描述了英国殖民者在印度如何努力通过他们的花园、进口植被,甚至为了打高尔夫和板球而在荒地上创建的运动场来改变景观。
现在想想任何帝国建设类电子游戏的基本机制,地图都是至关重要的。游戏玩法的关键促进因素通常是消除“战争迷雾”。对迷雾的掌控将决定游戏内的权宜之计以便重新设计地盘,并能够在游戏地图上建造建筑物。与非数字游戏中的地图板相比,Lammes和Wilmot(2013)总结电子游戏地图为一种“导航界面,[其]不仅仅是‘模仿’环境,而是通过具体的游戏规则在导航中转变它们。”历史上一个不可避免的平行现象是西塞尔·罗兹的话:
想到那些你在夜晚头顶看到的星星,这些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的广阔世界。如果我能,我会吞并这些行星;我经常这样想。看到它们如此清晰而又如此遥远,这让我感到悲伤。(Hardt & Negri,2001,第222页)
有人可能会倾向于将其与《星际争霸》这款游戏进行比较,这款游戏讲述了在银河系遥远角落的行星殖民故事。
在对《海岛大亨》空间性的理论化中,Magnet(2006)将游戏的空间展示为“一个被殖民的游戏景观,通过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双重话语唤醒其玩家”,并着手“指出游戏意识形态基础所伴随的危险”(第143页)。作者遵循路易·阿尔都塞的观点,将“唤醒”视作玩家被游戏现有的意识形态,即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所“召唤”。
在对帝国建设类游戏的分析中,Lammes补充道,“通过探索、贸易、制图和军事行动等殖民统治技巧,玩家创造了他们所拥有的个人殖民过去和未来。”在Lammes的分析中,Magnet所说的“游戏景观”变成了“后殖民游乐场”。
Lammes(2010)认为,这些游戏可能不是关于前殖民地文化在当下如何处理其殖民过去,但它们仍然是后殖民的,因为这是一个“更复杂的术语,涉及殖民文化的遗产如何以混合和变形的方式在当代文化中回响”(第1-6页)。虽然这是一个有效的讨论切入点,但Lammes的论点未能考虑到来自印度次大陆、非洲和中东的数百万玩家,对他们而言,这些帝国建设类游戏实际上提供了一种直接的方式来接触他们的殖民历史。
不过这些游戏对殖民地的描绘往往过于简单,包含了那些来自被殖民地区的玩家一眼就能看出的不准确之处。例如,即使是一款经过精心研究的游戏如《帝国:全面战争》,也有一些非常明显的缺陷:忽视了印度文化的多样性,仅提及“印度的做事方式”;茶园的出现比英国在1824年发现阿萨姆茶早了一个世纪;后来的靛蓝种植园没有被提及,而这些种植园曾引发了很多民众抗议;在莫卧儿帝国地图上没有伊斯兰教宗教中心;贝纳雷斯,印度教的圣城,被描绘成“伟大的静修院”,而实际上这里并没有这样的存在,而且静修院在历史上是非常不同的机构;最后,十九世纪的马拉塔帝国被描绘成使用印度国旗——而这个国旗直到1947年才正式使用。
电子游戏的地图也是一个可以创造替代历史的空间。在这里,可以逆转殖民过程并征服曾经的帝国强权。正如Lammes(2010)正确指出的那样,游戏中的地图制作具有高度的个人参与性:“在《帝国时代》中,地图获得了混合和个性化的特质,完全不同于殖民文化希望展示其权力关系的方式”(第1-6页)。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以下是《帝国:全面战争》论坛上的一条评论:
“我玩普鲁士的战役,到1735年,马拉塔不仅征服了印度、波斯和阿富汗,还从海盗那里夺取了安提瓜。到1740年,他们实际上通过波罗的海航行,登陆库尔兰,并在登陆后的回合中摧毁了他们。这实际上是有利的,因为它给了我一个借口在不与邻国开战的情况下占领库尔兰,同时我建立了防御工事,但到1750年,任何历史现实主义都早已消失。”(Den of Earth,2010)
那么,如何解读这种殖民主义的逆转呢?这里显然存在一种可能的后殖民反应元素(可能是无意的)。类似地,在殖民强国离开非洲后的早期,有人建议“非洲人应该坐下来用方尺重新绘制地图”(Ramutsindela,2006,第128页)。
然而,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论述的那样,策略游戏地图的重组特性比简单的重新绘制殖民地图要复杂得多,正如后殖民主义本身要复杂得多。在这里,介绍Edward Soja的“第三空间”概念是很有启发性的。这个概念来源于Henri Lefebvre对感知、构建和生活空间的分类,并且物理的、制图的和体验的空间应当在一个人的空间理解中同时运作。Soja在Lefebvre的“生活空间”基础上提出了他所谓的“第三空间”。他将第三空间描述为“现实与想象的空间”,在这里不可能将由空间感知所构建的想象空间与其物理和制图层面分开。根据Soja(1996)的说法:
“第三空间……植根于这种重组和激进开放的视角中。在我称之为批判性他者化的策略中,我尝试打开我们的空间想象,以应对所有的二元对立,任何试图通过引入“他者选择”(即将非我的选择设为他者,和同我的选择对立)来将政治思想和行动限制在仅有的两种选择中的行为。”(第5页)
在打开空间想象时,他引入了“他者”的选择,以挑战早期帝国空间概念的中心-边缘二元对立。在第三空间中,还涉及到社会中常常被传统空间表征所忽视的边缘部分。同样,在《帝国:全面战争》中,游戏地图经常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回应:当帝国奔向工业进步时,玩家发现自己意外地要应对叛乱,正如一位玩家在游戏论坛上抱怨:“我只是想知道如何阻止地区的叛乱,我在里面有满员的驻军和将军,并且免除了他们的税收,还解雇了一些部长,但这没有解决问题”(atco,2009)。存在于生活空间层面,这是Soja所指的第三空间。正如后殖民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中一样,这个抗议的第三空间在电子游戏帝国中是一个问题,正如在现实生活中的对应物一样。即使通过赢得游戏并征服整个电子游戏地图空间,也不可能消除他者——即持续存在的抗议,正如游戏动态地图空间中npc角色的生活继续。在她的后殖民批判中,Spivak指出,即使在英国帝国结束后的印度,问题仍然存在,去殖民化本身从底层无产阶级或属下阶层的角度来看是一个误导性的词语。对于Spivak(1993)来说,这些空间“没有与帝国主义文化交通的既定机构”,而且“不属于所谓的有组织劳动或逆转资本主义逻辑的尝试”。所以对于Spivak来说,去殖民化在没有较优越精英的逻辑规则的其他群体中,比如底层无产阶级,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正如前面提到的,他们这些群体,才构成了属下阶层。
- 关于属下阶层性和抗议的简叙
在谈论网络文化中的属下阶层时,Radhika Gajjala(2014)问道,“属下阶层何时被带到网络上,以及这是为了什么目的?”(第29页)这也是本文将探讨的问题,但在与Gajjala在其书《网络文化与属下阶层》中讨论的资本和在线小额信贷有关的属下阶层主体并非在同一平面上。Gajjala将属下阶层定义为“没有工具或没有积极地、自由的参与社会秩序权利的个体,[且]属下阶层被认为是没有为自己发声权利的”(第161页)。这一定义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游戏文化中的后殖民元素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积极”和“自由”的理解需要具体说明。当然,如果考虑到《魔兽世界》(WoW;暴雪娱乐,2014)服务器上的打金行为1,也许这个描述非常适合于那些无名无姓且毫无自由玩游戏的边缘玩家。
然而,这种露骨的相似性可能并不总是显而易见;在他的文章中,罗伯托·卡萨尔(2013)指出,“霸权斗争在电子游戏中非常活跃”(第332页)。卡萨尔指出,像《美国陆军》这样的游戏建立了霸权场景,其中一个主导群体(美国士兵)相对于那些被构建为他者和敌人的人(阿拉伯人)是极具优越性的。想象一个伊拉克玩家在玩《美国陆军》(2002)或一个来自扎伊尔的玩家在玩《孤岛惊魂2》(2008):游戏规则在限制他或她遵循游戏内容对其文化的某些假设并接受重新赋予的身份,而他或她作为游戏所构建的边缘人物,无法提出抗议。
在不同的场景中,有一些游戏,尽管很少且不为人知,但明确反对主导秩序: 在《围困中》(Under Siege,无正版中文翻译),Afkar Media(其开发者)试图通过庆祝反犹太复国主义抵抗的英雄主义来戏剧化并重新讨论1999年至2002年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事件。Afkar Media想表达他们的游戏不是宣传工具,[并且]由于媒体通常妖魔化穆斯林,他们这作者只是想试图讲述自己的故事。(Cassar,2013,第346页)
另一个例子是《Bhagat Singh》(2000)游戏,它是印度最早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之一。游戏中,主角是一名印度自由斗士。他的敌人是英国殖民统治下的警察。这又是一个反对殖民霸权的明确例子,但它显然不是“沉默”的。这个例子说明的问题在于那些以更积极和直接的方式抗议霸权的游戏是否可以被称为属下阶层。
在某些定义中,这些游戏即使是在电子游戏行业和全球游戏文化中也确实是“来自下方的声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通过发声,这些游戏已经在后殖民讨论中突破了边界。无论如何看待它们,像《Bhagat Singh》这样的游戏都成为了意识形态上抗议的平台。根据葛兰西的“缝合”概念,Cassar(2013)认为这些游戏“更接近被压迫阶级,因此当特定意识形态立场发生变化时,它们的反应更快[……]并可以以互联的方式展示主导和从属意识形态”(第247页)。
- 游戏玩家作为被殖民者/殖民者:电子游戏中的后殖民身份
在《刺客信条:自由呐喊》(2013)中,玩家扮演一位在十八世纪海地遇难的黑人水手。在那里奴隶制是普遍存在的。一个层面来说,游戏通过玩家游玩主角提供了一个对奴隶制进行积极的抗议。在另一个层面上,游戏中你解放的奴隶们表现出了一种无声的回应。虽然玩家无法从奴隶的角度体验游戏(除了一小部分主角伪装成奴隶的情节),但玩家扮演的主人公的身份其实也相当复杂。无论玩家本人是不是来自曾被殖民的国家还是其他地方,他们扮演被解放的奴隶转为的海盗都是处在一个“不自在”的位置。具体来说玩家不得不成为“他者”。殖民地的管理者在面对当地“土著”的过程中也会与自身身份作斗争。一方面来说,管理者和土著需要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如金普尔的金(Kipling’s Kim)或阿拉伯的劳伦斯(Lawrence of Arabia)等欧洲人也曾以印度人或贝都因人的身份出现(意味着管理者和土著的身份出现重叠)。《印度绅士礼仪指南》宣称: 印度绅士,尽管要对自己保持自尊,但不应进入为欧洲人预留的车厢,就像他不应进入为女士预留的车厢一样。虽然你可能已经习得欧洲人的习惯和礼仪,但要有勇气表明你不为自己是印度人而感到羞耻,并在所有情况下都认同你所属的种族文化。(Hardiman,1920)
这里的矛盾显而易见。尽管鼓励印度人习得欧洲人的习惯,但传授的教训是要与自己的人待在一起——一种相当冲突的观念。正如本文开始通过现实人物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来考察地图学和帝国主义一样,引入另一位现实人物来介绍后殖民身份的概念也很有教益:T.E.劳伦斯上校,更广为人知的是“阿拉伯的劳伦斯”。在大卫·里恩(David Lean)的同名电影中,劳伦斯身穿贝都因谢里夫(Bedouin sherif)的长袍,甚至穿着被英国同伴称为“黑鬼衣服”的衣服走进军官食堂。然而,在电影的后半部分,他对阿拉伯伙伴说:“看,阿里,看。(他捏了捏自己白皙的皮肤。)那是我。它是什么颜色的?那是我,但我对此无能为力。”(Lean,1962)。在殖民体系中,殖民者和被殖民者对自己的身份都感到不安、疑惑并感受到威胁。
在丽莎·中村(Lisa Nakamura)关于网络空间中种族问题的开创性工作中,她有通过一种可以视为与上述描述的殖民地英国的刻板印象平行的方式来探讨在线身份构成的问题。她指出,“刻板印象”本身是一个来自机械学语言的词。她引入了一个新词,“网络刻板印象”(cybertypes)来描述数字世界中的类似现象。早期的网络理论家(如谢丽·特克尔(Sherry Turkle))似乎认为监管和压迫性的社会规范(如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与用户在屏幕外的“单一、坚实”的身份有关。其实我们抛开身体这个框架获得更多“流动身份”后,反而获得了开辟新的且较少压迫性的规范的能力,并同时也获得了以更有效的方式“承认多样性”的能力。(Nakamura,2002,第13页)
Nakamura(2022)对此表示不同意,她指出由信息技术所提供的身份选择,如网络化身、整容手术和跨性别手术以及身体改造和其他网络义体,并没有打破单一身份的框架,而是将这个单一身份转移到“虚拟”领域。这个虚拟领域并非没有自己的法律和等级制度。所谓的“流动”自我并不比“坚实”自我更少受到文化霸权、行为规范和文化规范的约束。(第4页)
游戏研究已经指出,游戏设计在定义种族和身份时往往反映了殖民主义的逻辑。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对《文明》(Sid Meier’s Civilization,1991)的批评突出了游戏中的殖民扩张模型和高加索种族优越的假设。根据加洛韦的说法, 《文明III》的算法[...]抹去了历史上存在的许多人,例如因纽特人、爱尔兰人等等;它将文明与特定的民族或部落身份混为一谈,忽略了如非裔美国人或犹太人等的混合性和散居问题。(2006,第98页)
Nakamura 注意到在《魔兽世界》中某些角色类型在游戏中遭受种族歧视,而杰西卡·兰格(Jessica Langer)认为游戏涉及类似于现实世界中的权力和等级结构的构建。殖民地居民和其他边缘化人群——在这种情况下是魔兽中的部落——主要被描绘成肮脏、无组织的[和]原始的(例如部落中的巨魔、兽人和牛头人)。(Corneliussen & Rettberg,2008,第91页)
上述方面显然是“他者”的殖民构建。然而,在《魔兽世界》中扮演部落中的角色或在《自由呐喊》中扮演阿德瓦勒时,玩家都进行了一次“成为他者”的体验。在后殖民背景下,殖民者采取被殖民者身份的体验同样值得关注。根据萨义德(1978)所述, 这好似一个想要认为一切皆有可能的幻想—即可以去任何地方并成为任何人。T.E.劳伦斯在《智慧的七柱》中一再表达了这种幻想。他提醒我们,作为一个金发碧眼的英国人,他也可以像一个阿拉伯人一样在沙漠中穿行。我称这之为幻想,因为正如金普尔和劳伦斯不断提醒我们的那样,没有人,尤其是殖民地中的白人和非白人,会忘记“成为本地人”或操作“大游戏”是基于坚如磐石的基础框架,即欧洲的权力。难道曾经有哪个本地人被蓝眼或绿眼的金普尔和劳伦斯欺骗而视其为冒险家特工吗(即所有本地人都清楚欧洲人的嘴脸)?我对此表示怀疑。(第44页)
Nakamura将这一段话用来框定她在网络平台和电子游戏中“身份旅行”(Identity Tourism)的概念。在她早期关于网络游戏的文章中,她提到玩家在MUD向多人线上文字平台(MOO)中扮演东方刻板印象的角色(关于这一点将在下一部分详细讨论):“对于我上面描述的身份旅行的实践者来说,Lambda MOO代表了一个幻想的帝国空间,就像金普尔的英属印度一样,提供了一个可以上演‘成功探险的宏大梦想’的舞台”(Nakamura,1995,第181页)。
在电子游戏中,后殖民身份的冲突问题即使在殖民联系不那么直接的游戏中也被感知到:在《马克思·佩恩3》中,玩家需要在巴西贫民窟中奔跑,并几乎无休止地射杀屏幕上出现的大量巴西黑帮。虽然玩家扮演马克思·佩恩,但玩家可能并不是游戏假设的白人男性。事实上,玩家甚至可能是巴西人。中村所说的身份旅行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明显:玩家可以选择九个可玩的男性化身。有趣的是,九个化身中有五个来自与殖民有关的地区:海地、巴西、北爱尔兰、阿尔巴尼亚和毛里求斯。其中之一,Quarbani Singh,是个有趣的角色。Singh辛格被描述为毛里求斯人,但从名字和外貌来看,他似乎是来自北印度的旁遮普锡克教徒。这里注意,被带去毛里求斯种植园工作的契约印度移民也来自北印度,但不是来自旁遮普。
《孤岛惊魂2》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未命名的非洲国家,这个国家似乎曾是一个前殖民地。一本Edge杂志的评论将这个地点描述为“有着弹坑般坑洼道路的非洲,那里有生锈的AK-47,毫无价值的货币,尘土飞扬的贫民窟,炙热的贫困和无法摆脱的疟疾”。
这个故事不断与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之心》相联系,甚至有一个关卡以这本小说命名。不同之处在于,这次深入非洲的旅程不是由小说中的白人马洛(Marlow)或其电影改编《现代启示录》中的本杰明·威拉德上尉(Captain Benjamin Willard)开启的。而是由玩家扮演的夸尔巴尼·辛格(Quarbani Singh)作为一个后殖民主体在后殖民地场景中进行探索。然而,这种探索也是一种身份旅行——试图“理解”这个未命名的非洲国家后殖民创伤的身份,这个国家有血钻贸易、疟疾困扰的贫困,以及两个派系之间的权力政治。它们分别是劳动与解放统一阵线和人民抵抗联盟。两个派系都宣称是为了自由和抵抗强权,这是在殖民和后殖民世界中非常重要的情感因素。然而,两者都雇佣外国雇佣兵。尽管声称是抗议,但实际上他们是新的精英阶层。当扮演辛格时,玩家从社会的底层开始游戏。但一段时间后,游戏让玩家分别为每个派系效力,最后需要在派系之间做出选择。扮演辛格时,玩家在国家的不同地区执行任务,并获得血钻作为奖励。那些钻石似乎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在大多数任务中,派系否认与主角的任何联系,玩家必须在几乎匿名的情况下完成任务。玩家偶尔会见到本地神父。他会提供疟疾药片,但前提是玩家帮助他不幸的教区居民们获得离开国家的文件。事实上,玩家与深受苦难的(属下阶层?)平民的互动很少,而真正接触时,这似乎也是为了获取疟疾药片这一游戏机制的一部分。对于作为后殖民主体的辛格来说,他的身份在参与底层与精英活动之间进行着持续的对抗。对于玩家来说,受辛格的背景影响,身份体验早已更加复杂。正如在里恩的电影中,劳伦斯穿着阿拉伯服装,被同胞蔑称为“黑鬼”,同时意识到自己不可能成为阿拉伯人,充其量只是一个身份游客。在电子游戏的后殖民背景下,玩家也在努力弄清自己在游戏中究竟处于何种身份。
面对这样的身份危机和同样令人困惑的地缘政治,同时游戏又在其中穿插伪史和重构的地图,这会推动一种强烈的需求去迫使促成一个解决方案。最简单的方法是依赖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就像重新定位一张实际的地图(也称为“定向”)一样,地缘政治和身份地图都被殖民霸权系统“调整”。身份游客的二元性被自信的刻板印象所取代,正如在《印度绅士礼仪指南》的摘录中所看到的那样。
- 东方主义与电子游戏
萨义德将东方主义定义为“以东西方之间的基本区别为出发点,围绕东方及其人民、习俗、‘思想’、命运等进行详尽的理论、史诗、小说、社会描述和政治叙述。”事实上,东方的构建有助于定义西方和欧洲文明的本质。在阐述这一过程时,他指出:
通过对其(‘东方’)的陈述,授权对其的观点,描述其,教授其,安置其,统治其,东方主义成为一种西方主导、重构和掌控东方的方式。简而言之,由于东方主义,东方不是(也不是)一个自由的思想或行动主体。(萨义德,1978年,第38页)
无论是殖民地管理员学习印地语和波斯语以管理殖民地,还是坐在家里的欧洲人通过德拉克罗瓦的画作欣赏异国的东方,或是学习“大博弈”并与“本地人”混在一起的金(Kim),东方的形象总是在被制造出来,只代表殖民帝国主义希望展示和看到的事物。这间接的影响了地图的绘制方式和身份的固定。中村(Nakamura)准确地识别了她在电子游戏中发现的身份旅行中的东方主义现象。
她指出,“在MOO(多人在线文字游戏)中,绝大多数男性亚洲角色都符合流行电子媒体(如电子游戏、电视和电影)以及流行文学类型(如科幻和历史浪漫)中的熟悉刻板印象”(Nakamura,1995年)。这些游戏中的角色名字如春丽和刘康(在《街头霸王》中)“给予了用户理解从流行媒体中获得的东方战士形象”。Nakamura认为:
这是流行媒体进入网络空间的交叉效应的一个例子。作为最新加入电子娱乐媒体阵列的成员,游戏是各种图像和模拟的拼凑。完整的东方男性形象,配有剑,证实了东方男性强大、古老、异国情调和过时的概念。(1995年)
这种构建在电子游戏中的非西方角色塑造方式中显而易见。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以印度角色为特色的早期电子游戏之一是《街头霸王2》(Capcom,1991年)。在这里,达尔西姆被描绘成以“瑜伽”姿势踢腿,穿着破烂的橙色短裤和骷髅项链,以强调他的东方印度神秘色彩。他可以喷火球,悬浮,喜欢咖喱和冥想。为了增加他的东方形象,他非常保护他的儿子达塔和他的妻子,她的名字竟然叫莎莉(Sari,印度女性穿的服饰)!在以印度为特色的帝国建设游戏中,也可以看到一组经典的刻板印象。除了与《帝国:全面战争》中的不准确之处有关的观点外,还出现了更多的问题,例如《帝国时代3:亚洲王朝》(2007年)中创造的刻板印象。在这里,有一个严重的错误,即把印度士兵(殖民军中的印度士兵)视为一个种族社区,并且婆罗门祭司被描绘成骑象的战士。当像伦敦和洛杉矶这样的城市在电子游戏中被如此精心地描绘时,《杀手:沉默刺客》(2002年)中的“寺庙城市伏击”关卡却只能让主角在仓库之间移动,并最终遇到一个自动人力车司机。还有更奇怪的是,《使命召唤:现代战争3》(2011年)中的任务“Persona Non Grata”设定在喜马偕尔邦。虽然到处可见印度自动人力车,但在英国突击队与俄罗斯恐怖分子的枪战中,印度军队或任何印度人似乎都决定袖手旁观!
最近的《刺客信条:婆罗门》图画小说的创作者非常满足于二手知识和宝莱坞电影来构建他们的印度形象:
遗憾的是,我无法亲自前往印度直接研究这个故事。我不得不依靠大量的阅读,长时间观看宝莱坞电影,以及在这里与印度侨民的零星会面来澄清历史和文化细节。(Sophie,2013年)
不出所料的是,这些游戏中的印度的表现是有缺陷的,并依赖于刻板印象。即使是在《孤岛惊魂2》(2008年)和《刺客信条:解放呐喊》这样的游戏中,这些刻板印象也在起作用,这些游戏如前所述,试图有意识地与后殖民主义问题进行互动。两者的刻板印象都涉及前者中的非洲平民和后者中的奴隶,主角要么拯救他们,要么解放他们。这些非玩家角色几乎没有什么话要说,也没有任何机制可以积极抗议,他们在这些游戏中已经处于底层位置。然而,我们对他们底层身份的感知通过游戏机制本身得到了进一步构建:在这两款游戏中,他们的自由成为收集积分和升级的来源。玩家解放的奴隶越多,游戏允许解锁的升级越多。从表面上看,解放精英阶级控制的奴役的这种精神实际上成为了在游戏中生成资本的机制。游戏的“解放”和“拯救”规则集因此有效地转变为玩家和NPC的霸权系统,并在另一层面上将后者的身份定向化、刻板化,并被游戏视为人力资本。通过研究后殖民主义的三个不同方面——制图、身份以及这些方面如何通过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进行调解,现在可以得出一些关于玩家在参与游戏情景时角色的结论。
- 结论:重现后殖民主体
在分析某些电子游戏如何与后殖民主义概念相关时,有两位历史人物占据了重要位置。塞西尔·罗德斯作为卓越的殖民者,代表了被视为“文明使命”的帝国占有冲动。东方的建构及其刻板印象对于其占有和治理至关重要。在不同层面上,阿拉伯的劳伦斯代表了试图与被殖民者融合的西方社会一员,通过身份旅行体验成为东方主义议程的一部分。在电子游戏中,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地通过对身份和制图去探索与后殖民主义相关的问题,玩家都同时经历并跨越了上述两种类型的体验,并且质疑和重新思考游戏中身份的意义。
安妮亚·鲁姆巴(Ania Loomba, 1998)在跟随霍米·巴巴(Homi Bhabha)和其他评论家时指出,“殖民话语无法产生稳定和固定的身份[……](并)各种形式的交叉或‘混杂’和‘矛盾’”(第105页)。玩家在参与游戏时,既与向往游戏中支持的行为,同时也对其进行抗议。例如,只有通过玩《帝国:全面战争》,玩家才会(重新)构建殖民地图,并在创建另类历史时,不由自主的根据殖民游戏的规则进行另类历史规划。即使是在明确传达后殖民信息的游戏中,如《灰烬之下》和《巴加特·辛格》,表达观点的过程也是通过用另一精英取代之前的精英,从而有效地符合他们试图推翻的逻辑。同样,对身份旅行的批判也涉及亲历角色的扮演,这帮助玩家更有效的探索身份并认识到这种尝试的不足。无论是扮演阿德瓦勒与圣多明哥的法国殖民者作战,还是扮演马克思·佩恩在贫民窟中射击巴西人,玩家都必须扮演不是自己身份的角色。在任何情况下,根据玩家的背景和意识形态立场等,玩家既会有与所扮演的化身的互动,也有对该角色身份的质疑。如果后殖民是“写回去”(反抗),那么它是涉及殖民装置的矛盾写回。这种矛盾包括“对殖民者的强烈厌恶和否定,但也包括对其的模仿”(Muppidi,2004年,第43页)。因此,电子游戏作为一个形象的隐喻让这种矛盾明显的更加完全:在游戏世界中可以写出替代叙事,但只能在游戏提供的系统内进行。无论玩家来自曾经的被殖民国家还是其他地方,玩家在参与涉及殖民主义问题的游戏时,都会同时进行书写和反写。电子游戏媒介同时提供了底层/属下阶层、抗议、精英主义和霸权的可能性;玩家的实际操作(游玩)会导致他们对后殖民更深层次的理解和体验。
注释:
- 牛津学习者词典(2010年)将“金币农场”定义为“为了在游戏中取得进展,经常作为金币农场公司的一份工作长时间玩在线游戏,并随后将游戏货币、宝贵物品或角色出售给其他玩家以换取真钱的行为。”这些游戏内货币通常由经济不发达群体(通常在东南亚和中国)生成,并由全球各地能够负担得起这些“货币”的玩家购买,而无需在游戏中通过玩来赚取。
图片引用:
Mukherjee, Souvik, Videogames and Postcolonialism: Empire Plays Back, Palgrave Macmill-ian 2017.
Rockstar Research: The Weapon-Wielding Gangsters and Special Police Commandos of M-ax Payne 3, https://www.rockstargames.com/newswire/article/ak14o883817258/rockstar-research-the-weaponwielding-gangsters-and-special-polic.html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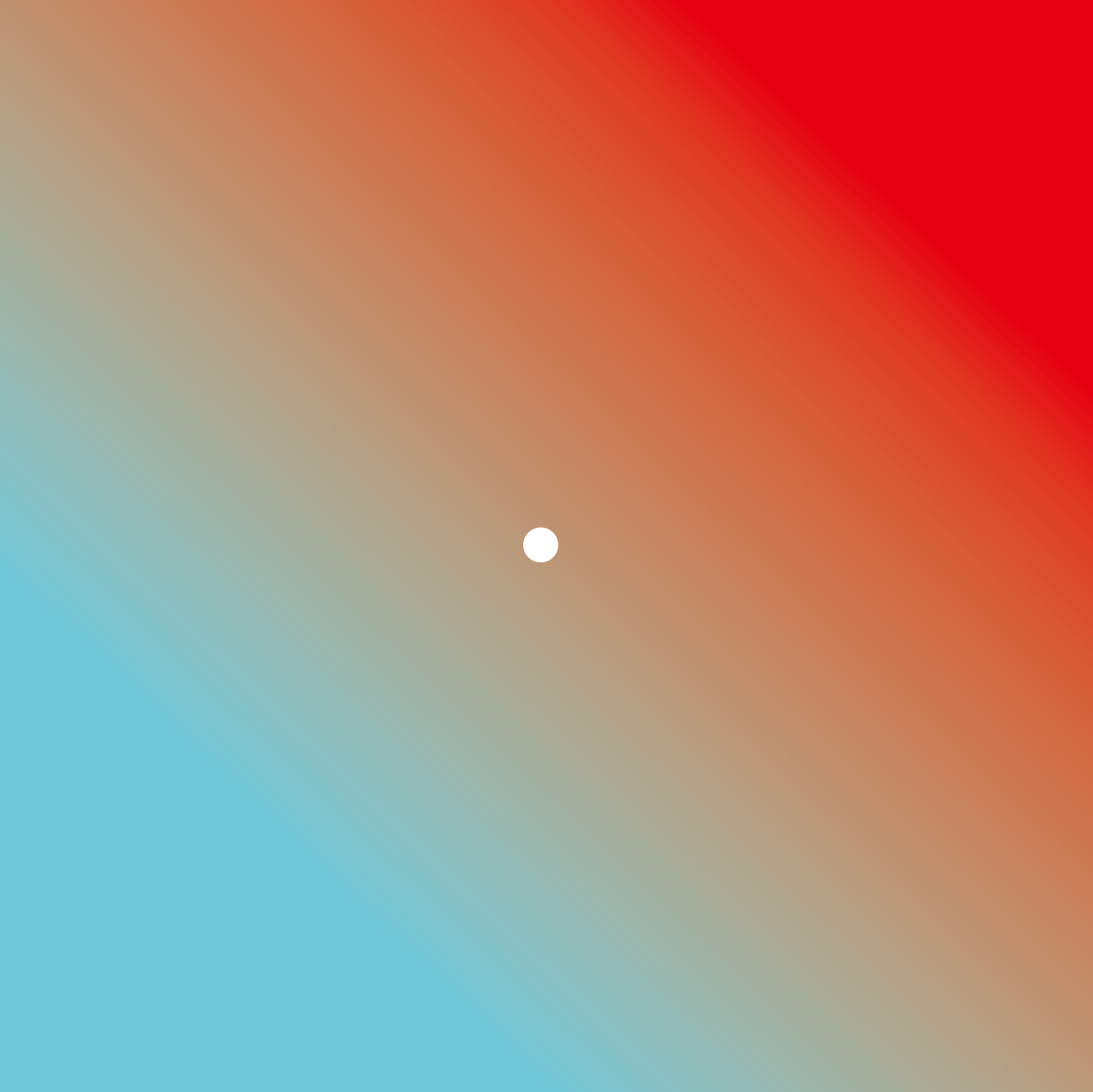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3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