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本文已收入日 | 落译介计划
译前言:
Puzzle这个概念本身其实不好译,即使只谈作为名词的puzzle game,在中文里它也对应到一大堆不同的东西:益智游戏、智力游戏、解谜游戏。也可以指解谜玩具和益智玩具,比如七巧板和华容道。也可以指那些纯粹形式的谜题,比如谜语和问题。本文讨论的几个游戏实例,俄罗斯方块、Drop7和Orbital,在旧有的中文分类中一般看作是“益智游戏”(顺便一提,这个名称也侧显了游戏在中文世界的文化困境,需要“益”智以正名),考虑到探讨的严肃性和puzzle一词本身的含义,统一处理为“解谜游戏”、“解谜”或“谜题”。
译自 Ian Bogost
How to Talk About Video Games,2015.11
Chapter13 ,pp103-110
松果 / 译
正文
正文
要讨论抽象的解谜游戏其实很难,特别是探讨为什么某些特定的范例能称为解谜游戏的杰作。我们可以讨论这些游戏的形式特性、感官美学、界面;我们可以讨论它们的新颖和创新;我们可以讨论它们游玩的挑战性。但对Drop7或者Orbital这样的游戏来说,这样的观察似乎只是隔靴搔痒。我们是否能够用和讨论《生化奇兵》(Bioshcok)、《吃豆人》(Pac-man)或者《模拟城市》(Simcity)一样的方式去讨论它们?无论是通过叙事、角色塑造还是模拟,这些游戏都提供了某种“关于性”(aboutness)。每个游戏都通过规则和环境,表现一些确凿的主题。
讨论抽象的游戏,难就难在它们不是确凿的。有些抽象游戏有着明显的实际主题,这给了它们诠释的切入点。比如,国际象棋,很明显是从军事冲突中获得灵感,不仅是因为它的历史渊源和作战的玩法,也因为它的棋子雕刻和命名。当一个骑士吃掉卒子时,很容易就能联想到作战的姿态。
而围棋则有点难以定性。正如哲学家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围棋的棋子,(和象棋)正相反,是小球、是圆盘、是简单的计数单位,只有一些不具名的、集体的或者是第三人称的功能:‘它走了一步’。它可以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只虱子、一头大象。”尽管人们可以把围棋的棋子想象成一个士兵、一头大象甚至一家沃尔玛,这个游戏的根本仍然是关于疆域的:谁占领得多,谁就赢。谜题会带来更多麻烦。有些逻辑和数学谜题采用了清晰的主题或者故事线,像“三间小屋谜题”。其他像数独这样的谜题却没有。大多数情况下,谜题在形式上完全是概念性的,表现出的具体性仅仅是一种意外。
一盒拼图游戏,完成后上面可能会印着一片风景或者一个汉堡,但这个主题和谜题本身并无关系。它只是一个皮肤,用来加速建构拼图的工作。对于一些可操作的谜题(manipulable puzzles),道理也是如此,比如七巧板。另外一些谜题则是完全抽象的,和世界上的任何存在和行动之间都没有明显的关系,比如纸牌接龙和魔方。
电子游戏从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解谜的传统。文字和图像冒险利用了逻辑谜题,特别是需要操纵物品来开门的谜题。我们也有大量的对传统的抽象桌游的改编。不过对当下的抽象游戏影响最大的,还是可操作的谜题,这有很充分的理由:“空间关系”有很好的可转化性,而电子游戏很擅长在空间中操作物体。但是当我们试图批判性地讨论解谜游戏时,问题就出现了:我们很难对谜题做出缜密的批评,因为谜题传递意义的方式并不像小说、电影、绘画那样。例如,连锁商店里的一副孔明棋(peg solitaire)并不具备宗教文本的功能。
理解抽象艺术的一种方式,是把它们看成隐喻或者寓言。在某些情况下,艺术品的名字有助于我们理解。杜尚的立体主义绘画《下楼梯的裸女》(Nude Descending a Staircase)迅速揭示了人形在运动中的多视角和叠加。蒙德里安著名的最后一幅作品《百老汇爵士乐》(Broadway Boogie Woogie)也是如此,它抽象地表达了纽约的喧嚣。
在别的情况下,作品本身并不能提供这样的助益,观者必须寻求自己的阐释。比如,蒙德里安的《带黄色块的构图》(Composition with Yellow Patch)就是这种情况,绘画的标题和画面里,都没有解释的入口。游戏,也很少通过名称给我们很多信息,主要是因为游戏和绘画史没有强烈的谱系学关系。然而,如果愿意的话,我们的解释能力还是让我们能从任何东西里读出意义来。
对于抽象的解谜游戏,最著名也最有代表性的解释是针对最著名的游戏提出:俄罗斯方块。Janet Murray在她1997年出版的《全息甲板上的哈姆雷特》(Hamlet on the Holodeck)一书中,将俄罗斯方块描述为“美国人超负荷生活的完美体现”。方块骨牌落下,像必须完成的任务、必须阅读的邮件、必须参加的会议。人们必须迅速行动,否则就会被淹没。但是检查完毕、归档完毕、或者满足要求之后,这个过程只会全部重来。没有安全退出的可能,只有注定的失败。
评论家Markku Eskelinen质疑Murray的说法十分荒唐:“Murray没有研究实际上的游戏,而是试图解释它的所谓主题,或者说,是把她偏好的主题投射其上。因此我们没有学到任何让俄罗斯方块得以成为游戏的特性。”一个苏联游戏竟然被解释为美国工作伦理的寓言,Eskelinen观察到了其中的奇异之处,并且提出,“如果有人因为有阶级、组织之分的黑白社群之间的持续斗争,性别不平等,受困的棋子没有医疗保险等等,就把国际象棋解释成一个完美的美国游戏,那也是同样离谱至极。”
不过,Murray的阐释其实是完全合理的。从文学或者艺术批评的角度来看,她提到了一些本质的东西:来自作品本身的根据。游戏制作于铁幕之后,这一点其实无足轻重。一部作品可以脱离它的创作语境,和全新的解释用无数种未曾设想的方式结合,哲学家德里达称之为“撒播”(dissemination)。没人能告诉你一件作品的“真正含义”,只要你能从文本中拿出证据来证明你的解释是合理的。
在讨论抽象的解谜游戏上,Murray和Eskelinen各自方法的问题是:一个希望游戏只通过某种叙事起作用,另一个希望游戏只通过形式起作用。但这二者缺一不可。问题似乎是在此:抽象解谜游戏的“意义”存在于其机制(mechanics)和动态(dynamics)之间的部分,而不是只存在于其中一个。
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在18世纪写就的美学巨著中,区分了“优美”和“崇高”。他把“美”和对事物形式的非逻辑、主观的判断联系起来,从想象力和理性之间的关系出发描述“崇高”。
康德描述了两种类型的崇高。“数学上的崇高”(mathematical sublime)是一种无垠或者浩瀚感,是由无限的“大”产生的反映。金字塔就是这种结构的的例子,它无法一眼窥得全貌;“力学上的崇高”(dynamical sublime)则是一种被压倒的感觉,它往往来源于自然力量,比如海边的悬崖或者巨大的雷云。数学上的崇高产生于巨大,力学上的崇高产生于畏惧。
《Drop7》和《Orbital》这类游戏的意义,从崇高的层面上理解是最好的,特别是数学上的崇高。
《Drop7》要求玩家将印有1到7的数字的棋子放置到7x7网格的各列中。在重力的作用下,这些数字会下落到底部或者堆积到其他数字上。如果一个棋子上的数字和它所在的行或者列上棋子的数量相同,它就会消失。灰色棋子要在解锁并显示出数字后才能消失,想让灰色棋子解锁,就要让与灰色棋子相邻的棋子消失两次。每次棋子消失都有分数奖励,连环combo和清场都有额外奖励。
《Drop7》中也有很多运气因素,游戏开始时盘面上已经有一些棋子。玩家要放置的每个棋子都是随机抽取的。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的是一个恰好需要的数字,让玩家能够实行连锁计划或者避免危险情况的出现;在别的情况下,一个不需要的棋子会迫使玩家改变计划。此外,灰色棋子出现时,其内容对玩家来说仍是未知,直到周围的棋子让它显现。总而言之,这些机制要求玩家每回合都重新评估棋盘的状态。灰色棋子可以被视为不确定因素,但这样做是不明智的。更好的做法是为最坏情况提前做好准备。
但即便如此,每一局游戏还是需要根据上一局游戏的结果和这局的盘面作出全面的重新评估。国际象棋和围棋中也有突发状况的存在,但《Drop7》让每一步行动的长期影响显示在所有玩家眼前,就算新手玩家也能看清。因此,玩《Drop7》所能得到的体验是,在一组缓慢变化的确定因素下,针对未来的或然情况做出当下的行动。可能情况的数量只能在一时之间数得过来,但很快就被新信息的随机性扰乱。这也正是玩家触及到这个游戏“数学上的崇高”之处。
对游戏的掌握总是暂时的,每一步棋都会让之前的无数可能性崩溃,然后形成一个全新的定局。但不像国际象棋或者围棋那样的持续变化,《Drop7》的每一步棋都会在之后揭示出关于自己的更多情况,因为之前属于未知的影响开始对现状施加作用。
在《Orbital》中,玩家从界面底部不停旋转的枪里发射球体。这些球体在墙面上和彼此之间不停弹射,直到惯性使其停止【译注:作者此处应该犯了一个错误。惯性并不会让运动的物体停止】。运动一旦停止,球就会开始膨胀,直到它们碰到墙或者另一个球,膨胀才会停止。玩家的目标是通过用新的球撞击三次来打破这些停止膨胀的球(每个球上的数字显示了当前的碰撞次数),从而得到一分。然而,如果一个球反弹到了玩家枪口上方的白线以下,游戏就结束了。为了契合游戏的宇宙主题,游戏里的球体会制造出影响后续球体轨迹的引力场。
像《Drop7》一样,《Orbital》的玩家也必须面对一个取决于不断增加的偶然性的游戏环境。游戏的策略之一是根据环境的摩擦力和引力去估算小球的轨迹。比如,玩家可以试着把球体聚集在角落里,这样也许一次发射就能摧毁许多球体。但是随着球体位置的确定,它们又会改变一部分游戏区域里的引力,这有效地抹去了玩家对于早期结构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就算玩家成功了,这种迷茫还是会出现,因为小球的爆炸同样会改变区域内的重力。
在《Drop7》里,数学上的崇高通过或然性进入游戏,即两种棋子的随机生成。在《Orbital》里,无论如何都没有任何的或然性,游戏里的所有运动都是可计算的,但是宇宙的变动不居让人类玩家无法做到这一点。玩家的每次射击都必须同时把握时机和物理,不论这次操作是不是预料之内的。《Orbital》是苛刻的,它把那条代表失败、轻触即溃的细线摆在屏幕上,《Drop7》则是慢慢地削减选择,直到失败来临。
玩《Drop7》和《Orbital》就像在推演弦理论,在评估无限未来的未知可能。不论一个人玩得好不好,这些游戏都迫使玩家审视系统——那个驱动游戏的系统、那个每一步都自我更新的系统——在数学上的无垠。
我们能说《Drop7》和《Orbital》这样的游戏是“关于”什么的吗?如果可以,又到底是“什么”?这时就有必要回到Murray对俄罗斯方块的阐释,毕竟人们可能会在俄罗斯方块的游玩中体会到类似的数学崇高。每个方块都会改变游戏的结构,玩家必须变换结构才能继续游戏,而几率决定了哪些形状能够被用来填补之前留下的几何空缺。《Drop7》和《Orbital》与之不同的重要一点是:它们是回合制的,而不是连续的。玩家必须参与其中来进行下一步动作,这是一个反思艰巨任务的机会,也是一种来自崇高的要求。
当Murray将俄罗斯方块视作一个关于工作的西西弗寓言时,她不是在说游戏有数学上的崇高的动态性,而是游戏操作的时间动态性。而“时间”,恰好是Eskelinen在反驳了Murray的叙事主义之后提出的正式解释。办公事务【译注:这里指俄罗斯方块所需要的、近乎工作的反复劳动】并不像《Drop7》和《Orbital》那样崇高,能快速产生分叉的平行世界,但它往往是一种对时间之箭的体验,对无法阻挡的过程的体验,无论是否取得结果。
在俄罗斯方块中,游玩的方式阻碍了我们通往崇高。但是在《Drop7》《Orbital》和中,玩家对崇高的沉思和反应却因为回合制的行动模式得到加强。每一步之间的停顿,都可能让感觉更富寓意,并将其视为游戏的主题。比如说,《Drop7》带来了一种体验:面对不可知的恐惧和渺小——不仅仅是对未来(等待放置的棋子)的不可知,而且是对过去(灰色棋子)的不可知。这种体验感觉很像,比如说,个人选择——一个人该向红十字会捐款吗?该皈依伊斯兰教吗?该找个情人吗?
要说清楚的是,《Drop7》的表层设计和模型实际完全没有这种感觉,但是这种关于数学上的崇高的经验在两个案例里都是相似的。从这方面,也许会有人说《Drop7》比《神鬼寓言》(Fable)和《生化奇兵》更加注重道德选择。虽然后两者可能模拟出了“决定”这一行为,但就像俄罗斯方块和“工作”的关系一样,他们没有更加动态地去贴近“选择”的主题。
《Orbital》建立在这一主题之上,但走向了完全不同的方向。在排除了随机性后,Orbital的主题围绕着“放置”(placement)展开。即便拥有关于宇宙物理的全部动力学知识(这个主题合适地寄身于游戏的视觉呈现),人类玩家在经过一定时间后还是太过容易犯错。就算是高手也会有欠缺。对此类游戏的这种阐释,也只是众多阐释中的一种,它们不会产生于游戏的机制,或者机制运行产生的动态过程中。相反地,它们形成于玩家在这二者之间寓言般地竭力感知的过程。
好的解谜游戏可以做很多事。但是根据成瘾性、深度、优雅性这样的特性——这是评判俄罗斯方块、《Drop7》或者《Orbital》这些游戏的常见价值维度——认为这些游戏是“好”的,就等于是在说抽象游戏只能对玩家施加冷血的、形式上的影响。而崇高,正是冷酷的形式主义的对立面:一种压倒性的、广阔和丰沛的感觉。崇高让我们看到自身理性的局限,向我们展示世界的变动和浩瀚。当然,这样的主题并不能被区区几个砖块、数字和形状的游戏穷尽,就像它也无法被区区几个关于战争、牺牲和失去的游戏把握一样。解谜游戏在数学上的崇高,就是要让我们抛开作为造物者和批评者的目标。我们通过把游戏和电影、绘画、文学这些熟悉的表现性艺术作比较,去发现什么是游戏的“杰作”。但是崇高也在别处:在建筑里,在自然里、在天气里。或许,我们也应从这些地方寻求启发。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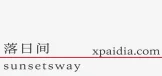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4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