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编者按
编者按
这是一篇我的演讲电子游戏的文化困境 | 落日间 引用与并从中受益匪浅的文章,Bogost一如既往犀利地指出了电子游戏在西方国家的形象问题:「自闭」与「排外」,被人所看不起。在他看来,似乎新时代的一个丰富多元的文化世界并没有到来,我们面对的是文化的碎片与分裂,而游戏就像是座孤零零的岛屿。
当玩家与之间甚至依旧充满对立与鄙视时,或许没多少人关注真正的电子游戏、电子游戏玩家以及开发者在外人看来的样子。
就像他所说的:「我们更迫切需要向我们的圈子之外派出更多的使节。否则,作为一个游戏的制作者,就会像作为游戏玩家一样,仍然还是显得很不正常」。
期待有更多开发者能发出自己的声音。
为什么除了游戏以外的任何事情都很重要 Why Anything but Games Matters(2014)
为什么除了游戏以外的任何事情都很重要 Why Anything but Games Matters(2014)
原文链接:点击跳转
翻译:叶梓涛
这是我在Indiecade 2014最后一天的主题会议上的简短演讲。会议的主题是 「为什么__」,发言人是我、Elizabeth LaPensée、Richard Lemarchand、Diana Santiago、Daphny David 和 Mattie Brice。我们每个人都讲了8分钟,说明为什么我们选择的东西对(独立)游戏开发很重要。
几个月前,我和一个技术媒体的朋友聊天。「有时我在思考在技术领域工作这件事」他开始说。他停顿了一下。「然后我想,至少我不是在游戏领域。」
他甚至没有用那种伏地魔式的「你懂得的」的指代(双方都知道但不明说的东西),而这的确是我们谈话的最初动力。这只是最新的例子。
但不只是这样,我认为他在谈论一种排外主义(provincialism)。
我的意思不仅仅是指老帽式的、刻板的游戏玩家形象,即在地下室里大口喝激浪的十几岁男孩,尽管显然这种形象仍然在流传。相反,我的意思是,游戏经常与其他形式的人类文化和创造性保持着一种隔离(separation)。
他们——我们——积极地培养和支持这种隔离,以便形成我们自己。
即使游戏已经变得越来越广泛,而它们也在自己内部进一步退缩。
在这个群体中——在屈指可数的成功的独立游戏节中的独立开发者——我们很容易拍着胸脯说,「但这里不同」。的确如此。
但是,它也不是。
想想我们发行和销售游戏的方式——特别是那些据称正在进行我们所宣称的表达性的革命(expressive revolution)的独立游戏。Steam 有时候使独立游戏在经济上可行,但它是通过重塑游戏的零售业来实现的——黑暗、怪异、令人尴尬的游戏商店被重塑为一个黑色和铁灰色的小小文字界面,所有更进一步的活动都被筛掉了。人们甚至不被允许在Valve的监督外运行游戏。遇见(新)游戏仍然需要对游戏粉丝(译注:“gamedom”-猜测为fandom的构词,或许指游戏论坛和媒体)宣誓效忠。
这就是我所说的排外主义的一个例子。
有游戏学位、游戏节、游戏零售渠道和游戏社区的坏处是——高估了它们的影响和冲击力。
是的,多样化的游戏在某种程度上是存在的,很多人都在做游戏,其中一些游戏往往能接触到大量观众。但是,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仍然是一个被内部成功的回音室所欺骗的小众(niche),以为我们正在接近主流。
事实是,普通大众下载的是他们在 App Store 上从朋友那里听说的,或者出现在排行榜前列的随便什么东西。事实是,游戏长期以来一直在对硅谷的亲近和对好莱坞的嫉妒之间徘徊,而它们实际上在这两个地方都没有找到归宿。
事实是,《我的世界》(Minecraft)是一款儿童游戏。事实是,我在为 "聪明的普通读者 "杂志写作的时候,写烧烤猪肉三明治(McRib)时,阅读我的人比我写《Flappy Bird》要多一个数量级。事实是,我们必须为游戏写作创建自己的小出版社(译注:此处链接为 Boss Fight Books,国内由读库引进第一期为《头目战》),因为你无法像在社交媒体上甚至在星球大战论坛上那样卖出一本普及游戏的书,因为游戏被认为没有受众。
现在,这不一定是一个问题。因为任何艺术形式都没有理由需要成为主流,而且确实很容易可以争论为什么不应该成为主流。但是,如果我们的文化地位感与现实相悖,那就危险了。
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仅限于游戏的现象。在华盛顿邮报上,阿丽莎·罗森伯格写到了她所说的「新文化战争」(new culture war)。「随着新文化战争的扩大,」罗森伯格说,「它也变得支离破碎,与其说是变成了巨大力量之间的冲突,不如说是变成了一系列棘手的游击冲突,以联盟的变化与新玩家的涌现为特点。」
以前,文化在大众媒体上打仗,赢了,也输了——想想麦当娜、巴特·辛普森和墨菲·布朗,现在我们在孤立的小众媒体爱好中打仗。罗森伯格认为这是一个意外的胜利。她宣称,「每个人都能赢得这场新的文化战争」,因为 「所有的故事都有机会被讲述」。
罗森伯格的说法的问题在于,分裂变成了巴尔干化(Balkanisation),而巴尔干化又变成了自由主义。相互敌视变成了 「做你想做的,只是不要把它强加给我」。如果被推到极限,所有的狂热爱好者都会变成种族隔离(apartheid)。
游戏的时代已经——可以说再次到来,在罗森伯格的新文化战争时代。因此,我们不仅是在自己内部内战,而且是在一个微小的、边缘的、饱受战争摧残的媒体中这样做,而它已经被 「发达」的媒体生态所抛弃。从外部来看,人们对电子游戏的预言与他们对苏丹的预言一样。
这种状况应该让我们感到羞愧。它应该修正我们先前对工作视野的理解。
例如:如果你想为游戏的多样性而奋斗,那么你绝对应该为玩家、创作者和游戏角色形象的多元化而奋斗。
但还有另一种多样性:我们的兴趣和倾向(dispositions)的多样性,我们所维持的公司和启发我们的影响的多样性,我们所接触的人和团体、行业和材料的多样性。这与我们与世界有足够的交往有关,以至于我们不再可能被看作是一个甚至不值得反对,更不用说支持的狭隘落后地区。
我们在游戏中已经变得太舒服了。我们现在有自己的黑话,通过 Steam 和 Twitch 以及游戏实况(Let's Plays)、游戏节等等自己的习俗。
在这些资源存在之前,事物还在萌芽时是不足的,但也是更加好的,因为它不可能只在游戏的圈子里运行。我们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从绘画,从建筑,从广告,从计算机,从系统理论,从玩具设计,从文学。有时我们把这些联系视为包袱,甚至视为殖民主义(译注:这里指 Aaserth 的《电脑游戏研究,第一年》),但它们也提供了基础(grounding)。它们帮助游戏在更广泛的背景中扎根。它们将我们与基岩(bedrock)联系起来。
但关于更广泛的背景的问题是:新的背景或许不再可能了。我们不能拒绝它们,我们不能 "破坏 "它们或忽视它们,因为我们已经在上升的海洋中建立了自己的小岛。游戏可以独立生存,但也许只能以索马里的方式,作为一个独立的世界。游戏不是21世纪主导的媒介,因为21世纪没有主导媒介。只有炸弹碎片。
我们需要停止与这一事实作斗争,好像这是一场任何人都可以,而我们也可以赢得的战争。我们已经们已经制出木筏、驶离沉船的荒岛,并且成功登岸——别的荒岛。而且我们可以在这里创造文明。只要看看周围,这是一个惊人的社群,你可以选择让它成为你唯一的社群。
问题是,这是否足够?如果人们仍然可以逃脱说「至少我不是在游戏业中」,并使之成为一个人人会心的说法,我们会在乎吗?
我们可以成为游戏制作者和玩家,但不只是游戏制作者和玩家。在今天碎片化的媒体生态中,我们更迫切需要向我们的圈子之外派出更多的使节。否则,作为一个游戏的制作者,就会像作为游戏玩家一样,仍然还是显得很不正常。
封面图游戏:《The Messenger》
拓展阅读:
Brian Eno 生成性音乐 Generative Music
Chris Bell 面向友情的设计 Designing For Friendship
Espen Aaserth: Computer Game Studies, Year One 电脑游戏研究,第一年
Frank Lantz 游戏不是媒体 Games Are Not Media (2009)
Liz England 「门的难题」 “The Door Problem” (2014)
Steven Harmon「厕所难题」"The Toilet Problem” (2017)
Ian Bogost 为什么除了游戏以外的任何事都很重要(2014)
落日间是一个探索「何为游戏」与「游戏何为」的媒体实验室。
感谢朋友们:@小雨 @阿伟 @11 @昕仔 @某小熊猫猫 @少楠 @Bob傅丰元 @小河shan @希辰Xichen @小乐 @DC @Bynn @webber @绅士凯布雷克 @侯晨钟 @Minke @Roam @兜&敏 @KIDD @菲兹 @喵呜 @李喆 @特特 @Skellig @阿和 @某大王akak1dD @solsticestone @鱼片与花卷 @Stoney @树袋熊 @MrNewton @鸭脖拉罕 @松果 @五香丸子@纪华裕 @李朵拉 的赞助及所有关注者的支持!:)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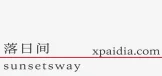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5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