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这篇文章很适合用来说明机核和重轻老师的牛逼
编者按
编者按
夸克、哈利-波特、主题演讲、单一麦芽威士忌、路虎、荔枝果实、爱情事务、脱引指针、齐泽克、玻色子、园艺师、莫桑比克、超级马里奥兄弟,都是公平的游戏。
这不是一篇掉书袋和充满文化资本的恶意文章。相反,Bogost 试图通过「掉书袋」来最终将掉书袋的智力/学术崇拜消除。
这应该是一篇可能到 2009 年为止讨论「游戏是什么?」这个本体论问题最全面也最时髦的回应。读起来像 Bogost 尝试站在哲学史的高度上来试图描述总结游戏研究中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时髦在于他结合了正在发生的哲学思潮,物导向本体论,而试图为游戏研究给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框架。
在他的讨论的意义上我被说服了。虽然在某种层面上,他「什么都没有说」,但至少他以一个外在的视角厘清了纠缠不清的「游戏学 vs 叙事学」的陈词滥调,并且展现了在那之后的学者的部分讨论,而我也期待中文世界的游戏讨论能早日跨过这个坑。
我不知道当时的台下有多少人听明白了,但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基底。
更重要的是,倘若我们能接受这种「平面的本体论」哲学视角作为背景开展对游戏具体的讨论,那至少不会出现所谓的学科和视角之间相互欺压的鄙视,或者对商业、设计、硬件、玩家的忽略,或对学术黑话的高扬。
玩家、哲学家、工程师、设计师、人类学者,大家或许都可以其乐融融地相处。
这是一个放荡的本体论(slutty ontology)
值得一提的是,Ian Bogost 的兴趣点在于某种物质性,这或许很接近于「媒介考古」的视角,而其提倡的软件研究,游戏「数字性」,以及更底层的「平台研究」毫无疑问是今天毫无技术力与创造性的人文环境所匮乏的。
而 Ian Bogost 可能是距离哲学家和学术传统最近的一位游戏设计师。或者说,他的游戏研究的思考得益于西方哲学学术传统,并目前来看有得以相接的倾向,你能够在与游戏无关的「物导向本体论(OOO)」的维基词条中看到他的名字,而这或许也变相地导致了似乎近年来他更多是作为哲学家,以及泛文化写作者来行事,附带一系列学术杂志、刊物的主编活动。
这是很少见的,他把自己作为信使而从游戏研究的地下室中走了出来。
不过有些惋惜的是似乎很难看到他的新作,早年开创 Persuasive Games 公司、制作《Cow Clicker》、还有雅达利主机上的诗歌游戏的创作行为似乎也看不见了。
或许有人会问,这是否回答了落日间「何为游戏」的困惑?
在操作层面上,是的,毕竟我想做的就是以各种创作、形态、讨论来扩大对电子游戏的定义,让更多的力相互交织混杂。
但本体论层面呢,则还没有,因为好的概念不仅要包容,更重要的是通过概念去创造,去引向新的认识,理解与可能性。
Ian Bogost
Ian Bogost
Ian Bogost 是一位作家和游戏设计师,他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电影与媒体研究项目的教授和主任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的教授,Bogost 还是独立游戏工作室Persuasive Games LLC 的创始合伙人,以及 The Atlantic的特约编辑,著有《Persuasive Games》《Play Anything》《Alien Phenomenology》等。他是MIT 平台研究相关出版系列丛书的共同编辑,还负责 Object Lessons 丛书和论文。
他的独立游戏包括《Cow Clicker》,这是一款《Facebook》游戏,以及 A Slow Year,是 Atari VCS、Windows 和 Mac 的电子游戏诗集,赢得了 Vanguard 和2010 年 IndieCade 音乐节上的 Virtuoso 奖。
电子游戏是一团糟
Videogames are a Mess(2009)
电子游戏是一团糟
Videogames are a Mess(2009)
原文链接:点击跳转
翻译:叶梓涛
以下是我在2009年数字游戏研究协会(DiGRA)会议上的主题演讲,该会议于2009年9月1日至4日在英国的 Uxbridge 举行。这些文字相当准确地符合于我在会议上的发言。在少数情况下,我添加了一些澄清,其中有额外相关的背景或评论。
如此多的电子游戏研究都被一个单一问题所标记:「什么是游戏?」
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的社区已经把这个「标记」理解为一种诅咒或瘟疫——一种形式主义的祸害,它吸引了,或者说仍然吸引着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远离了意义、接收和使用等更重要的事。
今天我想回到这个问题,「什么是游戏」?希望提醒我们它到底是什么:不是一个战略、修辞或政治问题,至少主要不是这样。相反,它是一个本体论问题。它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而不是领域建设的问题。也许是时候这样对待它了。
在更直接地回到本体论问题之前,让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我们作为一个领域的历史中的几个关键时刻。
很久以前,吸引我们集体想象力(和愤怒)的问题是这个:
电子游戏是一个规则的系统,或者是一种叙事?
我们非常喜欢这个问题,以至于我们甚至为它起了一个绰号:
游戏学 vs. 叙事学
像你们中的许多人一样,我以前也对这件事发表过一些看法。最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应该记住,是所谓的游戏学家选择了这些术语,而且他们做得非常优雅。
首先,看看这个词!Ludology。游戏学。在其所有的拉丁文的荣耀中,它给这种当时极不体面的以研究电子游戏为生的行为赋予了一种严肃性。
它也是历史性的,从 Huizinga 和 Callois 对 ludus 这个词的使用中汲取了灵感。感觉几乎就像你可以想象在毕业证书或名片上看到的东西。(译注:指的是 Huizinga《游戏的人》使用的 homo ludus 的古典游戏的词源作为「游戏学」的构词)
正如 Gonzalo Frasca 在六年前的第一届 DiGRA 会议上试图提醒我们的那样,但也正如我们可以从他1998年的 DAC 论文《游戏学遇上叙事学》(Ludology meets Narratology )中得知的那样,这两个概念从未打算以像「Ludology vs. Narratology 」这样值得在拉斯维加斯的侯爵标签中暗示的方式成为对手。相较于游戏学的「小麦可」,叙事学与其说是 「本田活塞」,不如说是 「路易斯医生」,它骑着自行车在前面行驶,怂恿游戏研究这个虚弱而不发达的英雄。
(译注:这里都是《拳无虚发 Punch-Out !!》的角色,小麦克(Little Mac)是作品中年纪最小的选手,本田活塞(Piston Honda)是对手,而路易斯医生(Doc Louis)是小麦克的教练,这里的意思大概就是叙事学与游戏学并不是旗鼓相当的对手的关系,而更像是叙事学被创造出去帮助游戏学)
正如 Frasca 所观察到的,游戏是弱势的。他正确地提出:「传统游戏的学术地位一直不如其他对象,如叙事学。」游戏学的提议并不涉及与叙事学进行一场重量级的较量,而是要向它学习,把它作为一种「研究对象如何变得合法」以及「研究本身如何变得成熟」的样本。正如叙事学的发展是设法解决叙事问题,也应发展某些新事物来设法解决游戏问题。
问题是,整个举动都只是一个伎俩。Frasca 认为,「必须发明*叙事学这个术语,以统一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们关于叙事的工作」。游戏学应该为游戏做同样的事情。他认为,这一举措应该解决游戏研究中的一个 「主要问题」:「缺乏明确的定义和理论;更多的是功能主义的方法,而不是形式主义;不同学科的分析支离破碎」。
但是 Frasca 把叙事学搞错了。它从来都不是一个统一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的术语;事实上,叙事学仍然是研究叙事的一种非常特殊的结构主义方法——注意这里不是故事(story),而是故事和它们讲述之间的差异。Frasca 最好说:「传统游戏的学术地位一直不如其他物品,比如海贝」。这样的说法可能会产生较少的误解。
然而,「叙事学」 框架的转移掩盖了真正的议程:朝着研究游戏的形式主义而非功能主义的方向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弗拉斯卡的标题「游戏学与叙事学的相遇」提供了被蒙在我们集体眼睛上的第一道阴影:这样的 「相遇」根本就不应该令人惊讶。一种形式主义的分析方法与另一种形式主义的分析方法相遇的想法,与其说是哑剧演员转变为泌尿科医生,不如说是律师重塑自己为立法者。一个小心翼翼的转折有效地重构了一个话语,发明了一个它永远不会输的冲突。这就像《蓝调兄弟》中的一幕,艾尔伍德在 Bob's Country Bunker 问酒保克莱尔:「你这里通常有什么样的音乐?」而她愉快地回答:「哦,我们有两种。乡村和西部。」
(译注:意思是当时西部和乡村音乐融合,其实这并不是两种音乐而是一种“The country music scene of the 1940s until the 1970s was largely dominated by Western music influences, so much so that the genre began to be called "Country and Western"”,用于说明其实叙事学和游戏学这个对偶其实本质上都是形式主义,并不真正有对立)
我强调这一点是为了让大家注意所谓的游戏学与叙事学辩论背后的真正目标。通过将一种形式主义与另一种形式主义对立起来,结果成为一个必然的结论:形式主义获胜。实际上,哪一种都不重要,因为基本假设是如此相似。游戏学/叙事学问题可能看起来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它更像是这样的问题。
游戏是否是一个规则系统,就像故事是一个叙事系统?
分歧已经消失,答案已经隐含(是)。大卫可以放下他的吊索,把石头扔回小河里。这第一种游戏的本体论实际上是一种修辞(rhetoric),根本不是一种本体论。它让我想起了齐泽克把伊拉克战争比作弗洛伊德的水壶轶事。
(译注:齐泽克用了一个笑话来讽刺伊拉克战争有着太多的理由从而显得这场战争是牵强的:弗洛伊德讲述了一个男人的故事,这个男人被邻居指责说他把水壶烧坏了,他反对并提出了三个论点(1):我从来没有向你借过水壶 (2):我还你水壶的时候它没有破 (3):我从你拿到这水壶的时候,它已经破了。比喻使用彼此矛盾的论点来捍卫一个核心论点,这些矛盾的论点彼此并列。它们被呈现为矛盾本身不存在。logique du chaudron[1] ,具体可参考齐泽克《伊拉克:借来的壶[2]》,大意就是 Bogost 认为游戏学和叙事学之争就如同是强行寻找借口而发起的一种修辞手法,让我想到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杜撰王敬轩来掀起虚构的论战而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力)
在这里,让我们注意到电子游戏本体论的第一步:暗示游戏本体论是一种形式的本体论:研究支撑游戏整体的结构和系统,游戏的类型或形式,整体意义上的及具体游戏的特殊案例。
正如 Espen Aarseth、Michael Mateas 和其他人所观察到的,对 「叙事学」(narratology)角色更好的描述是类似于 「叙事主义」(narrativism),Aarseth 描述为「这样一种观念,即一切皆为故事,讲故事是我们主要的,也许是唯一的理解模式,是我们对世界的认知视角」。叙事学是一种正式的分析方法,是实际的批评家在研究实际的故事系统和人工制品时使用的方法;叙事主义是一种从未被使用过的意识形态,但像所有的意识形态一样,在背景中驱动选择,被其干扰的主体甚至无法看到。
与游戏学的进步同时进行,但也延伸到游戏学之外的另一个思路是承认游戏似乎与故事叙述(storytelling)有很多共同之处。弗拉斯卡以游戏与故事共享的「许多元素」开始了他早期关于游戏学的文章,包括「角色、连锁行动(chained actions)、结局、背景设置」。在 3D Realms 开始开发《永远的毁灭公爵》的同年,Aarseth 写道:「声称游戏和叙事之间没有区别是忽略了这两个类别的基本性质。......区别并不明显,二者之间有很大的重叠」。
这一思想最值得注意的延续来自于 Jesper Juul,他从作为借来的水壶的游戏学中退了出来,认为游戏是由规则和虚构(rules and fiction)组成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即远离作为形式主义的叙事学和作为意识形态的叙事主义,而拥抱一种更加务实(pragmatic)的方法。正如 Juul 在《Half-Real》中所说。
.....电子游戏同时是两种相当不同的东西:电子游戏是真实的,因为它是由玩家实际互动的真实规则组成的;游戏的输赢是一个真实事件。然而,当通过杀死一条龙赢得游戏时,这条龙并不是一条真正的龙,而是一条虚构的龙。因此,玩电子游戏就是在想象一个虚构的世界时与真实的规则互动,电子游戏是一套规则,也是一个虚构的世界。
这里有两个进展。首先,有一个新的折衷论(syncretism)的接纳,一个由 Frasca、Aarseth 和其他人在言辞上提出但从未认真执行的接纳。Juul 认为,游戏可以同时是可玩的(ludic),也可以是虚构的(fictive),而不必放弃其系统性或虚构性的本质。
第二,出现了一丝渐变性。对于 Aarseth 和 Frasca 来说,叙述、角色和其他源自故事的元素存在于游戏中,但事物的天穹是形式的:它们背后的一个规则系统。Aarseth 说,当所有其他的东西都从游戏中剥离出来时,「规则仍然存在」。对尤尔来说,这个问题稍微有点细微的差异,但尽管如此,我们看到本体论的次序在地平线上出现。
Aarseth 温和的谩骂式叙事主义立场和 Juul 关于规则和虚构世界的更真诚的折衷立场都做出了一个共同的举动。
Whatever a game is, some part of it is more real than another. 无论一个游戏是什么,它的某些部分都比另一个更真实。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游戏本体论的一个新转折,也就是似乎没有人谈论的那个转折:观念论与实在论的冲突。我们可以对这在形而上学中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疑难,而它仍然是流行的且胡搅蛮缠的这一事实感到些许高兴。它提出了以下问题:现实的本质是基于我们头脑中的观念,还是独立于知识和意识单独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与当代思想相悖,Aarseth 和 Juul 对游戏采取了一种隐含的实在论立场,但却是一种麻烦的立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固定的独立概念,而是哲学家 Lee Braver 所说的对应性(correspondence)(A Thing of This World, pp.15-16):真理涉及思想与真实事物之间的某种对应关系。在 Juul 和 Aarseth 的立场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分层的区分。规则的形式结构是真实的,而像虚构和故事及这些规则的整体经验是在游玩及玩家的头脑中的副产品。
在这里,我们也发现了对观念论更熟悉的反应的痕迹,那就是康德式的超验主义(transcendentalism):当然,心智污染了我们对现实的经验,但这没关系:我们对于世界的知识并不反映事物本身,而是反映我们的感知与心灵中已经存在的原则的对应性。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 Aarseth 和 Juul 的立场:要么作为实在论的直接对应性理论,要么作为超验的观念主义,其中像故事这样的东西是由对已经存在的规则的观念的推理感知而产生的。在任何情况下,有一点是肯定的:游戏的某些部分比其他部分更基本,而有些部分仅仅是主体的(subjects)偶发现象。
我们发现在游戏设计的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运动。在 Hunicke、LeBlanc 和 Zubek 的游戏设计的机制动力学美学(MDA)模型中,游戏的「美学(aesthetics)」或体验是由玩家与 「动力学(dynamics)」的互动产生的,而「动力学」又是由设计师对机制(或规则)的构建产生的,其涌现行为产生了这些动态。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相同的对应性和超越性的怪异融合:游戏的现实是玩家感知的构建,但这种构建更根本地存在于与机制相对应的某个深层。
顺便说一句:在我们明天将听到的另一个进展中[也就是在会议的背景下,Michael Mateas 和 Noah Wardrip-Fruin 主张一个比机制更高序列的概念。他们把这个想法称为 「操作逻辑(operational logics)」,我把它描述为首先使特定的机制得以实现的结构。
总之,让我们把这称为电子游戏本体论的第二步:暗示游戏存在于多个层面,但有些比其他层面更真实。至少其中一些层次是心理的建构,而另一些则是物质的天穹,游戏在其形式层次上是真实的,但这种真实比它真正的真实更具有超验性。
最近,Juul 对游戏学术的现状提出了另一种看法。他认为,游戏学和叙事学的老问题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问题,他称之为“游戏/玩家问题”,简而言之,Juul 问道,研究的对象应该是玩家还是游戏?区别很简单:以游戏为中心的观点认为,游戏玩法驱动着玩家能做什么,而以玩家为中心的观点则认为,游戏玩法中发生的一切都由玩家驱动。
Juul 的观察也强调了社会科学的兴起,研究的重点是游戏玩家的社会实践,例如在美国的休息室和韩国的电脑房(PC Baang is a type of LAN gaming center in South Korea)中的游戏差异。因为这种方法对玩家的兴趣超过了游戏,所以他们也出现了帮助解释像大型多人在线游戏(MMOG)这样的多人体验。我们也可以把关于游戏作为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更少见的观点捆绑到游戏/玩家的难题中。我特别想到了 Alex Galloway 和 McKenzie Wark 的工作。
就 Juul 而言,他在这个问题上确定了两种立场,称一种为「隔离主义(segregationist)」(「游戏是独立于玩家的结构」),另一种为「整合主义(integrationist)」(「游戏是由玩家选择和维护的」)。在这里,各种其他因素都在发挥作用,可以说,这些因素通常不会在早期的形式主义或游戏的叙述中得到解释。Juul 提供了一些例子,从一个玩家通过《动物森友会》与她垂死的母亲关系的迷人而悲伤的生动故事,到一个人购买什么游戏机以及有什么游戏可以使用的根本选择。在这里,我们还发现了其他的混合型的工作,比如 Michael Nitsche 的游戏空间理论,其中游戏空间(也就是像沙发、地毯和电视柜这样的东西)的作用和游戏中的空间渲染同等,甚至更加重要。
正如「隔离主义者」这个含糊的贬义和历史性的标签所暗示的那样,我认为 Juul 的意思是认为游戏最好被认为是玩家和游戏的交融,但很难不看到这种思路中隐含的趋向:游戏实际上只是的软弱的皮肤,可能存在,但只以较弱的形式,直到它们被玩家填充和激活。
让我们把这称为电子游戏本体论的第三步:认为游戏在玩家占据了它们,并根据他们自己特定的个人和游戏背景来重新分配其形式的属性而赋予它们生命时存在。
我认为,此举是是对「康德式哥白尼革命」之于形而上学的一种相当直接的改编,在这种情况下,事物主要或专门为人类而存在,事物可能存在,但却无法脱离了它们的被思来思考这些事物。玩家群体中的背景、传播和差异的想法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就像它在过去几十年的文化研究中一样。
我想分享的关于电子游戏本体论的最后一个说法来自我自己最近与 Nick Montfort 关于平台研究[3](platform studies)的工作。用这个会议和组织为自己选择的名字来说,数位游戏研究的一个讽刺是,「数字」的东西在我们的谈话中是多么的缺席(译注:Bogost 所参加的这个会议名字为 DiGRA 数位游戏研究协会 (Digital Games Research Association))。例如,游戏学一直为自己接近「一般」的游戏而自豪。一些关于游戏设计的流行说法也是如此,包括Katie Salen 和 Eric Zimmerman 和 Tracy Fullerton。
(译注:前者指 NYU 教材《Rules of Play》,后者指 USC 的《Gamedesign Workshop》中文为《游戏数字梦工厂》)
Nick Montfort 和我想得出一个区别:电子游戏是计算性的人造物(computational artifacts),对它的理解至少需要部分地掌握计算机的架构。更强烈的是,每个电子游戏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在一个特定的计算机硬件上创建和运行的一个特定软件。这些软件和硬件系统单独或共同对彼此施加压力,向后延伸至灵感和影响,向前延伸至惯例和流派。我们希望这样的方法可以帮助支持社会的、批评的、物质的和政治经济的考量,而在此基础上去理解电子游戏等软件制品。简而言之,我们建议,计算媒体的一个主要的,甚至可能是首要的特征来自硬件和软件设计的限制。
在《Racing the Beam》(我们对 Atari VCS 的平台研究)的后记中,Nick 和我提出了一个关于计算性创造力(computational creativity)的研究模型。我们认为,它可以采取一些重点,我们区分了五种:
- 接受和操作(Reception / Operation)侧重于用户的体验,包括读者反应理论、精神分析和媒体效果研究等方法。
- 界面(Interface)侧重于用户与计算机系统的可见、可操作部分的关系,包括人机交互学科、视觉、电影和艺术史方法,以及像 Jay Bolter 和 Richard Grusin 的 「再媒介化(Remediation)」的概念。
- 形式和功能(Form and Function)着重于程序的运作和行为。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关于程序运行的方法。顺带一说,这里是游戏学和叙事学的所在地。
- 代码(Code)侧重于程序员的理解与编程工作方式,包括软件研究和代码美学,以及软件工程和其他用于理解代码如何工作和构建的计算机科学方法。
- 平台(Platform)则专注于代码下的抽象层。如果说代码研究是新媒体之于软件工程和计算机编程的类比,那么平台研究就是之于计算系统和计算机架构的(代码研究的)版本。
我们认为,对新媒体的有效研究往往会从这一模式的多个层次中汲取营养。但更强烈的是,我们认为我们称之为平台的分析层次既是有希望的,也是新媒体学术研究中未被充分探索的方面。
Nick 和我把这五个层次放在文化和背景的汤里,而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位于与人类文化和经验的复杂关系中。例如,我们对雅达利的硬件设计的大部分讨论涉及到1970年代计算机的商业和社会实践的背景。同样地,我们对特定游戏的讨论的重要方面涉及到工作和创造的背景和文化,包括像《Adventure》和《Pitfall!》这样的游戏的开发者在表达目标、文化影响和硬件平台本身的物质性限制之间的妥协。
对这种模式有一种可能的反对意见,我们当然不止一次地听到过。有人称其为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但更细微的抱怨可能会指责我们是科学自然主义(scientific naturalism)。对于自然主义者来说,世界相当于由更基本、更小的事物和部分组成的集合,而真正真实的事物相当于最基本的事物。物引向部分,部分引向元素,元素引向原子,原子引向质子,质子引向夸克,等等。科学旨在探究事物的底部,并继续挖掘,直到找到一个底部。
但是,我们的模型的目的并不是论证平台是游戏的根本,对硬件的仔细研究,直到金属,将为所有现存的游戏带来某些粒子雨的解释。相反,它的目的是表明平台是游戏中无可争议的一部分,假装它们不是,充其量不过是排外主义,最糟糕的是纯粹的疯狂。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想在游戏的本体论中提出第四步,包含并回应所有变化,我希望它能让我们所有人都满意并有所帮助。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必要在当代形而上学中快速迂回一下。
近年来,一小部分但越来越有发言权的哲学家一直在集合对后康德传统的反实在论(anti-realism)的批判。由于它与我的兴趣相关,这种批判涉及两个相关的进展:第一,对观念论的拒绝和对实在论的重申。第二,对存在的关注扩大到人类之外。
让我们从普遍持有的观点开始,也就是我们在上个世纪一直伴随着的观点,我们可以追溯到康德的超验观念论。这一立场认为,存在(Being)只为了主体而存在。对贝克莱(Berkeley)来说,它以主观观念论的形式出现,或者说,物体只是感知它们的人头脑中的一捆感官数据。对黑格尔来说,它以绝对观念论的形式出现,或者说,世界的最佳特征是它在自我意识的头脑中出现的方式。对海德格尔来说,物存在人类意识之外的,但它们的存在只存在于人类的领会之中。对德里达来说,事物永远不会完全呈现在我们面前,而只是在特定的背景下,无休止地对于个体进行区分和延迟。二十世纪中期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延续了现象学开创的对意识的偏爱,但将这种自负过渡到语言。
所有这些举动都把存在看作是一个访问(access)的问题,而且是人类的访问。甘丹·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创造了一个术语相关主义,来描述这种观点,即相关主义认为存在只是作为心灵和世界之间的某种相关物而存在。虽然对于一些相关论者来说,事物可以存在,但在梅拉苏的观点中,它们只是为我们而存在。梅拉苏在他2006年的书《有限性之后》中提供的主要例子是:相关论者不能接受「事件Y发生在人类出现之前的xx年」这样的论述。
「不,他将简单地添加,也许只是对他自己而言,但他会添加类似于一个简单的附注,总是同一个附注,他将谨慎地附加在这句话的末尾:事件Y发生在人类出现之前的X年,对人类而言(甚至,对人类科学家而言)。」 (p 13)
虽然这个概念可能是可理解的,但它只是通过重印在人类过去的认知过程而变得如此。在相关主义论者看来,人类和世界都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永远不会离开另一个而存在。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与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现代性批判类似的东西:它试图将世界分成人类和自然两部分。人类文化被允许是多种多样的和复杂的,但自然或物质世界只被允许是单一的。
梅亚苏和其他一些思想家以「思辨实在论」为标准,试图拒绝相关主义,重新承认存在的多重复杂性,并将存在从人类的唯一权限中解放出来,让其回归到所有的对象,包括人类。现实被重新确认,人类被允许与海胆、野葛、玉米饼、类星体和特斯拉线圈一起生活在其中。
这项任务有许多方法,但我最喜欢的,也是我认为对澄清游戏本体论最有用的,是格雷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的方法。从海德格尔的工具分析开始,哈曼构建成他所谓的「物导向的哲学(object-oriented philosophy)」。
非常快:海德格尔提出,物(objects)是不可能被这样理解的。相反,它们与目的相关,这种情况使得将锤子或玉米饼作为物来谈论是有问题的;这样的物体在被背景化(语境化)时是「上手」(或 zuhanden)。海德格尔进一步认为,当物不再将自己隐藏在这些背景中时,它们最能显现。他称这种状态为「在手」(或 vorhanden)。他最喜欢的例子是锤子,它提供了打钉子的活动,我们在追求一个更大的项目时,比如说建造房子时,会忽略它——除非它坏了,变得抽象了。
哈曼认为,这种「工具存在(tool-being)」是所有物体的真理,而不仅仅是「此在」Dasein 的真理:锤子、人、俳句和热狗都是随时随地的,都是「上手」和「在手」的。他建议,物体不仅仅是通过「人的使用」来联系,而是通过任何使用,包括一个物体和任何其他物体之间的所有关系。在这里,我们也找到了对科学自然主义的回应:事物被允许平等存在,无论其大小、规模或秩序如何。
关于这一切,还有很多话要说,但现在没时间了。你可能会注意到与我们共同的学科更熟悉的其他传统的相似之处,如怀特海在过程哲学中的 occasions 概念,或者拉图尔在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中的行动者概念。但是,也许总结哈曼立场的最简单的方式是引用他对 Lee Braver 的实在论概念的非正式补充:「人类/世界关系只是任何两个实体之间关系的一个特例」。我想澄清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特例」只是指一个特定的,而不是例外。
在把我们从形而上学的水池的清爽浸泡跳出晾干之前,我还需要游一圈,它通过 Levi Bryant 对哈曼的面向对象的哲学的改编,变成前者所说的平面本体论(flat ontology)。这是一个首次出现在曼努埃尔-德兰达(Manuel DeLanda)作品中的术语,他用它来指代完全由个体组成的本体论(而不是例如物种或属)。Bryant 对这个短语的使用有些不同:一个扁平的本体论允许所有物体具有相同的本体论地位。此外,就拉图尔而言,「对象」可以指有形的或无形的实体,包括意图的对象(objects of intention):夸克、哈利-波特、主题演讲、单一麦芽威士忌、路虎、荔枝果实、爱情事务、脱引指针、齐泽克、玻色子、园艺师、莫桑比克、超级马里奥兄弟,都是公平的游戏。如果称这些东西为「物(objects)」让你感到困扰,你可以用我的术语「单位(unit)」来代替它,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好了,终于回到游戏上来了。在我与你分享的所有关于游戏本体论的观点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共同的属性:所有这些观点都陈述或暗示了电子游戏对象的本体论等级。在某些情况下,这种等级是科学主义的一种,比如对新媒体层次的(错误)解读,或者操作逻辑、机械学、动力学和美学之间的关系。在其他情况下,这种等级制度是一种反实在论的自然/世界之分,如 Juul 的想象世界和真实规则,或玩家对游戏的应用和游戏本身。
如果我们接受哈曼和布莱恩特的邀请,使本体论领域扁平化,使所有对象处于平等地位,那么结果就是一个无差别的平面,在这个平面上,游戏存在的所有方面都有同样的可能性。然后我们可以提出的问题是,对于一个特定环境下的特定游戏,哪些单位是重要的?这样的策略使我们免于寻求何种游戏对象无可争议的依据,防止我们对计算机硬件或人类经验(或两者之间的任何东西)提出短视的本质主义,并迫使我们对特定的分析情况提出更具体的问题。对于「什么是游戏」这个问题,寻求一个答案应不再令人满意。
这不仅仅是号召我们大家和睦相处,也不仅仅是呼吁一个不明确的德勒兹式的内在性或集群(assemblage)的平面。这不是魔术,也不是空洞的理论。它是一种思考游戏的存在(existence)的实际方法。
举个例子是有必要的。我想,鉴于其中一些材料的深奥特性,最好选择一个大家熟悉的电子游戏,一个每个人都能立即意识到其重要性和品质的游戏。
什么是 Atari VCS 上的《E.T》?有很多方法可以回答。
《E.T.》是8千字节的6502操作码和操作数,你可以在 ROM 本身的十六进制转储中看到。每个值都与一个处理器的操作相对应,其中一些操作也需要操作数。例如,十六进制$69是增加一个值的操作码。
装配好的 ROM 实际上只是游戏汇编代码的重格式化版本,而《E.T. 》也是它的源代码,是一系列人类可读的(或者说是稍微可读的)机器操作代码的助记符,用于运行该游戏。
《E.T.》是一束射频调制流(RF modulations),它是由用户输入和程序流改变了被称为 TIA 的定制图形和声音芯片上的内存映射寄存器中的数据而产生的,它又被转化为无线电频率,与电视的电子束和扬声器一起运作。
《E.T.》是一个掩膜 ROM ,一个集成电路,其上的存储器(在这种情况下价值8k)被硬接到一个蚀刻的晶圆上。这类 ROM的光罩(photomask )设置成本很高,但好处是量产非常便宜,量产当然是电子游戏 E.T. 的主要特点之一。
《E.T.》是一个用螺丝钉固定的成型塑料盒,上面贴着一个胶粘标签,依次印有胶印标签。
《E.T.》是一种消费品,是一种包装在盒子里的产品,零售时有印刷的说明书和包装纸板,挂在钩子或放在架子上。
《E.T.》是一个产生某种体验的规则或机制系统,这种体验在某些方面与一个虚构的外星植物学家滞留在地球上的故事相对应,他的名字叫 E.T.,一群孩子试图保护他不受政府和科学暴力的仇外心理的影响。
《E.T.》是一个可以拥有、保护、许可、销售和侵犯的知识产权单位。
《E.T.》是一种收藏品,是一种绝版或「稀缺」的物品,可以进行交易或展示。
《E.T.》是一个标志,描绘了1983年崩溃的情况。在这个意义上,《E.T.》这个标志不仅仅是一个虚构的外星植物人,而是一个极端失败的概念,是「有史以来最糟糕的游戏」:它是的贪婪文化情结和设计约束导致了在阿拉莫戈多垃圾场的著名的游戏坟场,是随后被过度简化的替罪羊过程——换句话说,「E.T.」是 Atari 的 「滑铁卢」。
所有这些单位同时存在,但又彼此独立。没有一个「真正的」《E.T.》,无论是叙事的结构、特征和事件,还是产生它的代码,或者两者之间的任何东西。拉图尔称其为不可还原(irreduction)。「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还原成其他东西」,即使一个事物的某些方面可被认为是对其他事物的改造。
事实上,有一些工作是从这些视角中来看待游戏的,例如 TL Taylor 对《无尽的任务》,Seth Giddings 对技术文化,Bart Simon 对 Wii 的工作等等,我在这次演讲中的兴趣在于提出本体论的主张,而不是社会/政治的主张,这一点的进一步澄清需要行为者网络理论的突破。更多的内容可以在我2008年的《计算机游戏哲学》主题演讲中找到,更多的内容可见我即将发表的(2009年11月)SLSA 主题演讲。
拉图尔通过网络的概念来处理变换的过程,网络由行为者(可以是人或非人)的相互行为,进入和退出关系组成。我的「单位操作概念」提供了另一种模式,一个单位由一组其他单位(同样是人或非人)组成,不考虑规模,由一种类似于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的「计数为一」(compté comme un)的姿态构成。单位操作与拉图式的网络和行动者有着重要的区别,但我必须把这个澄清留待他日。
总之,这些进展使我们能够在相关主义(媒体研究和游戏的社会科学分析中常见的问题)和还原论的两难(对游戏的形式和材料分析的常见批评之一)之间行走。让我们考虑两个简单的例子。
关于相关主义,昨天我们听到 Graeme Kirkpatrick 争论说,游戏不能参与意义,因为它们的结构本身就与意义相悖(这发生在前一天的美学讨论小组中)。同样地,就在我去参加会议之前,游戏设计师 Frank Lantz 发表了他的论点:《游戏不是媒体 Games Are Not Media (2009)》。这样的观点拒绝了一些人(包括我自己)关于游戏确实能够建构意义和进行论证的主张。然而,平面本体论的好处是,我们不需要认为游戏只能表意,Graeme 、Frank 和我可以继续像迪斯科舞厅里的哑剧演员和泌尿科医生一样相处。
关于还原论,当 Jesper Juul 一年前[发现了《吃豆人》投币游戏的拆解程序 ROM 时,他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就是Pac-Man 的真实面貌吗?」 答案是肯定的,在某种意义上。《吃豆人》的代码在很大程度上是真正的《吃豆人》。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并不是《吃豆人》事物的全部。
同样,《E.T.》也从来不是刚刚提到的事物之一,它也不仅仅是所有这些事物的集合。矛盾的是,一个扁平化的本体论允许它既是又不是。我们可以区分「游戏即代码」和 「游戏即游玩过程」的本体论地位,而不必求助于某种作为形式、类型或超验的游戏的高阶概念。用 Levi Bryant 的一个玩笑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放荡的本体论( slutty ontology),在这个本体论中,任何东西都足以让人玩得开心。
同样地,关联主义的批判的一种解读方式不是拒绝关联,而是拒绝唯一的关联(对梅拉苏来说,存在-思想;对哈曼来说,存在-人类),接受多种关联,只要我们愿意或需要,就可以。当哈曼声称人与世界的关系只是任何两个实体之间关系的一个特例时,这当然是他的立场。如果我们认真对待放荡的本体论的诱惑,我们可能会预见一个本体论增殖的新时代。
这样的视角带来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游戏研究不仅意味着对游戏的研究,或作为游戏规则的研究,还意味着作为计算机的规则,或作为计算机的操作逻辑,或作为硅片的弹壳,或作为寄存器的指令,或作为无线电频率的电子枪的研究。而游戏不仅是为人类的游戏,也是为处理器、为塑料盒外壳、为盒式总线、为消费者、为记忆载体等等的游戏。这是一个完全没有探索过的领域,也是我最有兴趣探索的方向。
最后一件事:我们可以把这种杂乱无章的东西称为什么,它取代了我们以前对「什么是游戏」这个问题的过于简化的、等级制的和相关主义的答案?
尽管我想抵制拉图尔的存在只通过关系而存在的概念,以及他相关的网络的概念,我认为这些概念过于规范化了,但我们倒是可以采用他「乱局」imbroglio 的概念,一种「永远不清楚谁和什么在行动」的混乱(Reassembling the Social, p. 46),拉图尔最初的例子是与人类知识有关的,例如阅读报纸的方式使我们卷入了不同领域的纠结中,它们相互联系但又相互混合。拉图尔这样写道:
混合[报纸]文章勾勒出科学、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技术、虚构等方面错综复杂的局面。...... 所有的文化和自然每天都在被搅动,...... 但似乎没有人为此困扰。 ——《我们从未现代过》,第2页
但是拉图的「乱局」感觉太正式了,对我来说太有条理了。乱局是一种智力上的困境,这肯定如一团乱麻,但这团乱麻是戴着领带的。
也许我们可以采用演员网络理论家约翰-劳(John Law)的说法来代替。Law 讲述了一个故事,他与一位合作者进行了一个研究项目,两人调查了一家医院信托基金处理酒精导致的肝病患者的方式。正如在许多官僚主义的情形下,他们很快发现了其巨大的逻辑复杂性。在某些情况,而不是其他情况下,来自市中心咨询中心的病人被建议去治疗项目,但他们必须预约。然而,许多人并不这样认为,而认为它是一个随到随治的地方。Law 实事求是地总结说,这种情况是一团「混乱(mess)」。
Law 反思了作为方法论关注的混乱概念,这个概念抵制创造整齐的小堆的一致的分析。相反,有必要追求「非一致性(non-coherence)」。Law 说:「这就是谈论'混乱'的问题:它是那些痴迷于使事物整洁的人所使用的一种贬义词。相反,我更倾向于放松边界控制,允许非连贯性的东西表现出来。或者更确切地说,开始思考我们可能采取的方式。」
请注意 Law 的混乱和结构主义方法的形式主义之间的区别:它不是一些说明所有事情的总体系统操作,一套文化道德或一套在光亮的桦木地板上举行的特别精心安排的狂欢的规定,而是一个松散并快速的单位的结构化——为了——什么任何事,不仅仅是为了事件牵涉的人类演员。
混乱不是一堆东西,即使位于难以落脚的地方,也能整齐地组织起来。混乱不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优雅事物。它不是一个由穿着马甲的保险商评估和管理风险的智力项目。一团混乱是一堆不方便的、有时令人厌恶的东西。
它不像在波洛克或毕加索的画作中发现的那种混乱,而更像在凯因霍尔茨(Keinholz)的雕塑中发现的混乱。
混乱是意外(accident)。混乱是一种你在你不想要的地方发现的东西。混乱是当你错过了闹钟,抓住了水杯时,地板上一串串的碎玻璃。混乱是凳子上的一堆热乎乎的、看不见的狗屎,然后是凳子上和靴子底的。混乱是不优雅的,是杂乱的,是凌乱的,是恐怖的。我们对它感到畏惧,但它就在那里,我们必须处理它。
电子游戏是一团乱。
一团我们并不需要一直试图清理的混乱,如果有可能的话。
References
References
封面:选自《The Policeman's Beard Is Half Constructed》中 Joan Hall 所绘制的插图,在插图边上的诗歌是这样写的:
许多被激怒的精神病学家正在煽动一个疲惫的屠夫。屠夫疲惫不堪,因为他已经切了几个小时和几个星期的肉、牛排和羊肉。他不希望与狂暴的精神病学家一起吟唱任何东西,但他唱起了他的琴弦切除师,他梦见了一位宇宙学家,他想到了他的狗。那条狗叫赫伯特。 —— 计算机诗人 RACTER .1984
落日间是一个探索「何为游戏」与「游戏何为」的媒体实验室。
感谢朋友们:@小雨 @阿伟 @11 @昕仔 @某小熊猫猫 @少楠 @Bob傅丰元 @小河shan @希辰Xichen @小乐 @DC @Bynn @webber @绅士凯布雷克 @侯晨钟 @Minke @Roam @兜&敏 @KIDD @菲兹 @喵呜 @李喆 @特特 @Skellig @阿和 @某大王akak1dD @solsticestone @鱼片与花卷 @Stoney @树袋熊 @MrNewton @鸭脖拉罕 @松果 @五香丸子@纪华裕 @李朵拉 的赞助及所有关注者的 支持!:)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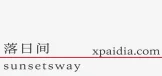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1 条评论热门最新